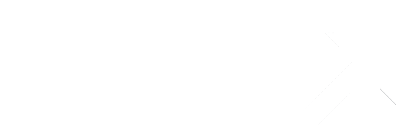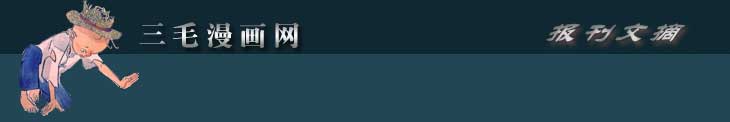
漫画家张乐平和台湾女作家三毛
—— 一段特别而难忘的交集
周立安
(作者简介:周立安先后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工作、任中国《桥》杂志社上海分社社长, 现任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采编部主任兼任《环球中医药》杂志社副社长,同时担任《二十一世纪中国观察与报告》丛书主编,主编出版多部反映中国 经济社会发展状态的新闻报告类作品。1989年4月,跟踪采访了第一次回归祖国大陆寻亲的台湾著名女作家三毛,所作录音专访《万般情深在故土——上海访台 湾著名女作家三毛》,获当年全国对台宣传新闻类作品一等奖。)
每年的一月四日和九月二十七日,对于我总是一个特别缅怀的日子,曾经的两个鲜活和对于我们的世界有过特别意义的生命——这是他们仙逝的时日。由于一个特 别的机遇也由于我的新闻人职业身份,中国大陆当代杰出的漫画大师、又被尊为“三毛之父”的张乐平先生和以“三毛”为笔名的台湾著名作家陈平女士,曾在我生命旅程的一个时光点上,有过一段特别有意义和难忘的交集。
一
一九八九年仲春时节,喜称自己是“唐人女子”的三毛,带着一身世界的风尘来到上海。这是她多年来第一次回大陆寻根,她曾在不同的场合说起过她这次来大陆的不平静的心境——“近乡情怯”,但她还是怀着最急切的愿望来了。
四月八日那天下午,我在张乐平先生家中第一次见到这位具有传奇色彩而那一刻脸上又泛溢着毫不掩饰的幸福光彩的“唐人女子”。
第一眼见到的三毛,很奇怪地看到她上身穿着的竟是一套男式的涤卡中山装。而这在当时的上海以至整个大陆都已经是过了时的服装。然而她似乎无论到了哪里也 不会忽略装载具有独特“三毛味”的东西。那件中山装穿在三毛身上,给人的第一感觉,她的身上确实有一种英气里融合着一股刚直和达观的豪气。说来也许有人不 信,那一天,她戴在手指上的一枚“戒指”状的饰物,竟是她在朱家角小街上买来的铜针箍,对这样一件过去时代民间妇女手工缝制衣鞋时用的顶针工具,她视为罕 物,大加叹赏地举起手来用上海话说:“漂亮口伐?”
可见,三毛实际上常以一颗平凡的心热爱一切她能体味出美的普通事物。这或许也是三毛才有的一种独特的审美观和文化意趣。
那天,落座后,三毛很爽朗地说道,这次到大陆来,为两件事:一是认张乐平先生为父;二是完成自己父亲的心愿,到舟山定海老家去祭祖省亲,同时取一瓶故乡海边的水和一抷故乡大地的土,带回台湾。所以,她首先来到上海,并且首先落脚在张乐平先生家里。
作为作家的陈平为什么将自己的笔名取为“三毛”,又为什么此一刻要急切地认张乐平先生为自己的父亲?
对此,三毛说,在自己三岁的时候,看了今生的第一本书,就是张乐平先生的漫画集《三毛流浪记》,那本书对自己产生很大的影响;后来等到自己长大了,也开 始写书了,就以“三毛”为笔名,作为对张乐平先生所创造的那个三毛的纪念。三毛说,在自己的生命中,是张乐平先生的书,使得自己今生今世成了一个爱看小人 物故事的人,她永远感谢张乐平先生给了自己一个丰富的童年。说着说着,她用刚学的上海话说:“爸爸是三毛之父,我是三毛,三毛不认三毛的爸爸,认谁做爸爸 呀?”那一刻,四十岁已出头的三毛,完全是一个忘情地在慈父面前撒娇的小女孩,并且是那样的纯情和自然,完全没有矫揉造作的痕迹。
二
对于作为台湾著名女作家的三毛认自己做父亲这样一件事,张乐平先生也认为这是自己生平中的一件快事,他说:“没想到我画三毛‘画’出一个真的女儿来,我 真的很开心!在这之前,一位素不相识的女士,一位负有盛名的女作家自认为是我的女儿,这太出乎我的意外了。但这一切,现在已经成真。”
张乐平先生说,自己知道作家三毛的时间不算短,大约是七八年前吧,有人向他讲起台湾有位女作家,以自己笔下的“三毛”作笔名,当时自己总不信,不信这个 笔名同自己画的三毛有什么瓜葛。后来,有人把一本杂志拿给自己看,上面确有她本人叙述笔名由来的记载,一些老朋友也给他证实了这件事。
张乐平先生很慈爱地给我介绍说,三毛是个极富有感情又极易动感情的人。她那诚挚而又炽热的感情不时感染着我们。她一到家,就情不自禁地吐露自己思念故 土、思念亲人的情愫。她对我们说,当她乘上回大陆的飞机的时候,内心就翻腾得厉害,但强制自己不要让夺眶而出的泪水坏了淡妆过的容颜,可是飞机一着陆便再 也控制不住横流的热泪了——索性痛痛快快地哭出声来!她说自己实在太激动了。
三毛此时也陷入一种极端的忘情中说:“飞机一着地,就强烈地感觉到,就要到家了。尽管近乡情怯,但能不激动么?!现在我到了爸爸身边,但有时还会觉得就像在梦中一样。我好幸福噢!”
在我们的交谈中,三毛不时地对着张乐平先生一口一个“爸爸”地叫不停,令人强烈地感受到她内心里对于此行认亲成功的满溢的幸福感。而对此,她丝毫不掩饰。
张乐平先生也不掩饰自己内心里对于这个来自台湾的女儿的喜爱。他说,三毛到达那天,自己从电话里知道了她要到家的准确的时间,尽管自己身体不太好,还是 早早守在弄堂口盼望她的到来。而三毛一来,就完全像到了自己的家,一点生分也没有,爸,妈,叫个不停,像久别重逢的亲人。她曾深情地对自己说:“爸爸,谢 谢您创造了我的笔名。”
在交谈中,三毛特别绘声绘色地说起一件很让她高兴的事。
来上海前,她曾来信表示希望能有一件卡其中山装。而那时的当下,谁还穿中山装呢,市场上几乎已经绝迹了。还是张乐平先生的大儿媳帮忙,跑了好多地方,终 于觅到一件涤卡中山装,这也就算是张乐平先生给她的见面礼。当她拿到这份见面礼时,高兴得像个孩子,立即穿上身,冲到镜子前,一个劲地左照右照,说太合 身,太好了!说到这件事的时候,三毛又用洋泾浜上海话说:“我一边照镜子,一边对爸爸说:爸爸,侬看,我漂亮口伐?”此时的三毛神态,又俨然是一个纯情的 小女孩,那样的开心,那样的忘情。
三
在数度的交谈中,我深深感受到她内心里自然存在的对于自然、对于生活和对于生命中所有美好点滴的敏锐感受和深沉的挚爱。
一次,谈到她到上海郊区青浦朱家角镇去游览的感受,说着说着,就很动情起来:“我走过世界很多地方,就我们中国的江南最美,昨天我发现了这个地方,又是 好美好美喔……”当我们谈起当下有一些年轻人对人生的意义感到渺茫,甚至不珍惜自己的生命,她也在我没料到时突然激动起来,说:“生命是最值得珍惜的!” 一边说,一边在我夫人托我带来请她签名留念的她的一本散文集的扉页上利落地写下两个字:“活着”!这都是三毛最素朴最直接的情感表达。是一种方式,也是一 种天性。
对于此,张乐平先生在此后他所写的一篇回忆性文章中,也曾有过这样一段叙述性文 字:“三毛,一个饱经忧患的女性,学的是哲学,熟谙三种外语,跑过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原先在我的想象中,她是个传奇式的人物。可是相处的四天,却是如此 容易亲近。她的性格、脾气、爱好像谁呢?看她那乐观、倔强、好胜、豪爽、多情而又有正义感,有时又显出几分孩子气,这倒真有几分像我笔下的三毛。”
一九八九年的那个难忘的春天,以“三毛”为笔名的台湾著名女作家陈平千里来沪寻父,被传为文坛佳话。这也给晚年的张乐平先生平添了几多亲情与欢乐,由 此,张乐平先生在自己生命的最后的晚年,也为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倾注了巨大的热情。其实,除了张乐平先生,由于女性之间更易于情感交流。这次在三毛首次回 大陆的过程中,在张乐平先生家共住了四天,三毛与张乐平先生的夫人交谈得更多。张乐平先生的夫人也深深爱着这位远道而来的“女儿”,她给我们也讲了许多关 于三毛在他们家的故事,言语中充满了疼爱之情。在三毛去世后的一九九一年下半年的一天,张乐平先生夫人还向我说起过,一九九〇年下半年三毛最后一次从她家 回台湾时还对他们说:“爸爸,妈妈,到春节的时候,我会回来跟你们一起过年。”但怎么也想不到不久后传来的却是噩耗。到此时,张乐平先生夫人还陷在深深的 悲痛与怀念中。
对于我,在一九八九年仲春的那几日中,除了见证到了张乐平先生与三毛这对父女曾经的美好时光,还收获到了一些至今珍藏的无价念想之物。
也许由于张乐平先生对于我们对他和三毛的父女相认相逢盛事所表达的真情祝福感到欣慰,又或许斯时张乐平先生内心里也有巨大的幸福感愿意表达,在我离开他 家之前,他特意在手边的几张A4规格的纸上一口气为我画了四幅他画了一辈子的漫画形象的三毛。陪在一边的张乐平先生的儿子阿四说:“周先生,你真幸运,我 爸爸因为身体不好,这些年已经封笔不画了,今天是他太高兴了。”
这一年,张乐平先生八十高寿,由于患病,手抖得厉害,或许正因为这个原因,张乐平先生一下子给我画了四幅,大约有努力画出他心目中更好的一幅的心思,可见张乐平先生对于自己的作品从来都是一丝不苟的。
见张乐平先生画了画,站在边上观赏的三毛也来了兴致,说:“我也在爸爸画的画上添几笔吧,写什么呢?”她歪着头,像在思考着什么。其中一副写道:“愿大家快乐,健康,勇敢,坚强,乐观。三毛共勉”
四
那一年代,我们这些人的政治观念还是很强的,我立即想到这应该可以成为促进两岸和平统一事业的一件具有一定历史意义的见证物——“三毛之父”与女儿三毛 珠联璧合在同一张纸上永留隔空阻不断的心心相印之中华传人血脉相通亲情——而这应当可以通过相关传媒作为彰显和传扬的佳事。
想到当时由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的对外宣传刊物中国《桥》杂志社这一比较高层的平面媒体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传播渠道,同时也委托我作为他们的兼职记 者提供相关稿件,于是,我讲了一个大概的意思,三毛欣然应许,在其中的一张中写下她的一段话语:“中国‘桥’——文学就是心灵的桥梁。”在落款“三毛”的 下方,她也与张乐平先生一样,署上了日期:“一九八九年四月七日”。这里,或许三毛连日沉浸在欢乐的亲情中,时光的概念已经有些忽略。那一天准确的日期, 还是张乐平先生写得对,应当是一九八九年四月八日。几天中,她除了与张乐平先生共叙父女之情,还与张乐平先生夫人彻夜谈心;有几个白天则去逛了龙华寺,还 去了青浦淀山湖畔的大观园、朱家角以及邻近的昆山周庄。说起那几天所经历到的事和所看到的一切,她一径地就说:“好开心噢,就像在梦里一样。”
“文学就是心灵的桥梁”,这段文字实际上深刻地表露了三毛的心迹——细想一下,在过往的几十年中,作为台湾著名作家的三毛与作为大陆漫画大师的张乐平, 实际生活的空间轨迹从来未曾交集过,但无论在世界何方“流浪”,三毛的心中始终有着一个坐落在上海的家,那里有一位她从童年时代起就一直尊崇和心仪的慈祥 父亲;三毛与张乐平先生,一个著文,一个作画,“三毛”这一艺术形象及其与中国文化的紧密关联,就像一座桥梁,连接起了三毛与张乐平先生的心灵与情感。
五
如今,斯人已逝,睹物思人,这也是他们留给我的最珍贵的纪念,我想,这也许是他们两位在他们生命接近最后的时光中携手在同一张纸上留下的父女心灵与情感交集的难得的见证物——对于今天,除了纪念,还有历史。
我至今还清楚记得第二次与她在她上海堂哥家会面时谈起当时年轻人的生活和思想,以及她曾经的浪迹天涯的经历时的情形,她很庄重地对我说:“对于一个人, 心无归所才是真正的流浪,心无所属才是真正的死亡。”这两句话,至今仍是我真正认识、探索三毛这位“唐人女子”精神世界和真性情的重要密钥。
二〇〇四年初夏,我在舟山定海采访,专程去到建在三毛祖宅的三毛纪念馆参观,并将我珍藏的三毛声音资料赠送纪念馆。那一刻,在沙滩边习习的海风中,三毛 写过的那首《橄榄树》的歌声,仿佛伴着细微的海浪袭岸声续续传来:“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同时,我仿佛又一次听 到在海天间传来的三毛那清纯和热烈的话音:我是一个永远的“唐人女子”……我们不说再见,因为我还会回来。
——摘自2012年3月4日《新民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