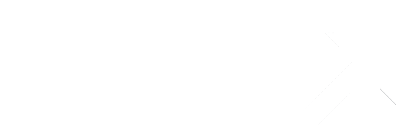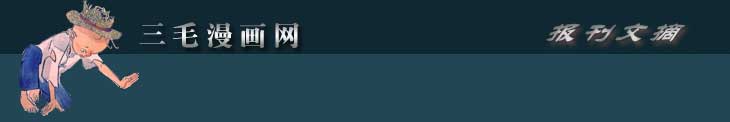
成人与孩子、肉体与精神的饥饿
金兆钧
音乐剧《三毛流浪记》已经成功上演。诚如很多朋友看过所说的:这不仅是一部给孩子看的音乐剧,也是一部给成人看的音乐剧。
《三毛流浪记》能给孩子们看,在于编剧吃透了张乐平先生原漫画文本中的两个字:温暖——事实上,三毛的经历始终处于极度的悲惨之中。无论怎样,他总是“倒霉透顶” ,天下之大,他始终得不到他最低的要求:一个烧饼。然而无论怎样,他总是坦白、真实、淳朴,善待他人,以一己的纯净照耀着一片黑暗。因此,孩子们看得懂,他们可能对三毛真实的生活处境没有体验——现在营养过剩的孩子们很难有体验,但他们绝对能够感受到三毛始终简单而善良的内心。正如剧情说明中所言,不论怎样,创作者们还是留下了一个“据说”的光明结尾。能够把原著中带泪的笑以音乐剧的方式在今天表现,是此剧第一层文本的成功。
《三毛流浪记》能给大人们看,在于编剧关山始终不变的人文情怀。诗人出身的关山有一种执拗,从早期参与实验性话剧的创作开始,他坚持要把智性的思考融入一切可能的表达。这既赋予了他的创作的深刻性,无疑也有画地为牢的危险。这正是《金沙》和《蝶》剧中漂亮的歌词和晦涩的剧情之间构成的悖论。而在《三毛流浪记》中,关山有了变化。这种变化在于他仍然坚持着智性的高度,却摇身一变混入了尘世中,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剧中种种情节的设置,首首歌词的咏叹,深入浅出。若愿琢磨,无论强拆、城管,还是黑道老大、疯魔记者,无不令人粲然而会意,如不愿深究,则孩子们的呼告,母子间的低语,又无不令人怆然而涕下。扬善斥恶,直指人心,在陈述三毛极度肉体饥饿的同时展现世间的精神饥饿,则是此剧第二层文本的成功。
三宝也在变。 《蝶》剧观后,我曾笑说他把一辈子学到的本事都用上了。美则美矣,但分量过重,容易让人吃不消。 《三毛流浪记》中,三宝大踏步后退,唱段设计以民谣体为主,甚至没有一段大的咏叹调。然而,这种做法却以简胜繁、拨四两而动千斤,反而收效甚佳。观戏当晚,我身后一个不过十来岁的小男孩听上去似乎看过一场,当晚几乎一直跟着在唱所有的唱段。孩子的音乐记忆力固然惊人,三宝的旋律入耳入心也可见一斑。这种以简单结构、易于上口的旋律辅以丰富的调性调式变化结合管弦加电声乐队的编配,恐怕是音乐剧音乐写作中值得重视的手段——既使观众容易把握重要音乐主题,又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听觉体验。在对比极度悲惨的情节演进中,音乐始终充满了温暖。此应是《三毛流浪记》第三层文本的成功。
在张乐平先生原著的基础上提炼出“饥饿”为核心贯穿全剧是非常聪明的选择,反观近年来不少音乐剧包括歌剧往往采用了电视剧式的编剧思维,线索过多,交代不清,短短的两个多小时的舞台时空中无法使观众集中精力直接介入剧情。开个不算玩笑的玩笑,有时候我们还真可以反思一下“三突出” :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抛开此原则在当年实践中的恶果不谈,却也是依据舞台艺术总结出来的有益经验。 《三毛流浪记》正是做到了在所有人物中突出三毛等三个小孩的“正面”性,在三个小孩中突出了三毛,表现三毛又突出了他的纯朴和善良的品质。有了这样的设置,才达到了少长咸宜、扣人心弦的剧场效果。
虽然如此, 《三毛流浪记》也还留下一些遗憾。由于以张乐平先生的原著为基础,是点描式的结构,缺乏一以贯之的情节线索,仍然有浓重的散文化色彩,因此戏剧性冲突的演进受到影响,前半场仍显得拖沓了一些。此外唱段设置由于大多使用民谣体,主题唱段的重复似乎还可以更强化些——也是“三突出” ,能够有像《当下》这样的唱段在音乐剧演出后能够独立“上市”流传,恐怕也是音乐剧成功的重要标志。
瑕不掩瑜,何况好戏是演出来、磨出来、改出来的,《三毛流浪记》有很好的运营,也就有不断在巡演或驻场演出中千锤百炼的机会,希望在今后的巡演中该剧能够十年磨一剑,尽善,并且尽美!
——摘自2012年2月27日《中国艺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