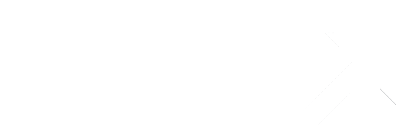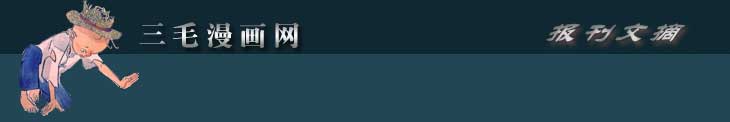
“三毛老爷爷”
沈建中
既无师承又非专门研究的我,近来总在叨念“大师张乐平先生百年诞辰了!”——多少有些痴迷,小三毛亦古稀过五,有哪段时事脱过班呢?初于小康日脚,接着“从军”“流浪”,“迎解放”,“翻身”成了“好儿童”,“学雷锋”“爱科学”,乃至跨世纪后“特奥会”、现今“世博会”,都要插一足,还被改成电影电视、动画广播、连火花也无数枚。民国漫画人物少说有鲁少飞的改造博士、叶浅予的王先生小陈、黄尧的牛鼻子、高龙生的阿斗,梁白波的蜜蜂小姐等,曾有严折西《漫画界全体明星大会串》记录风靡一时盛况,可只有三毛活到现在,难怪专家魏绍昌、叶冈一锤定音:要说漫画人物的生命力,三毛顶长寿。大家美誉大师为“三毛之父”,喜欢的读者数不清,我也是这份甜蜜的受惠者,那就寻个理由来套近乎,我的称呼却是:“三毛老爷爷”。此虽出于髫龄记忆,可老人家年长我半百,焉能不尊“老爷爷”乎?!私心揣度“老爷爷”比“大师”更亲近些。
一
像千万拖鼻涕穿开裆裤时爱上三毛一样,山西北路近苏州河弄堂口老虎灶旁的小人书摊,一分钱看二本,二分钱借回家,三分钱借五天,我在那里看了好几本三毛小书,《流浪记》、《今昔》当然有,连解放前《外传》、《从军记》都有,印象最深是一本破烂不堪的,成长后才晓得乃上海杂志公司印行《三毛·第一集》初版本。我发现三毛“从军”前并不孤苦,穿着绒线衫,脚上圆头皮鞋,整天跟小妹妹跳绳玩皮球,嬉闹时滑稽发噱,捣蛋时耍点小聪明,老爸是富态商人。这让我感觉很富有,生怕别人不晓得,能在小友间炫示;直到不惑之年购得一部精装“全集”,见没收录战前三毛,每每惋惜。
小时候“追星”还算文雅,仅四处寻觅小书报刊上的三毛,小友间互相卖弄故事,或者弄些发蜡沾点水,把头发塑成三毛;最多跑到五原路,躲起来盯梢“老爷爷”进出;一位同学很神秘地告诉我,“倒是没见着,但伊屋里哪能有嘎兮多小人,闹猛得不得了,会不会是收养了嘎兮多三毛。”有人讲他会在三角花园溜达,去了几次,连背影都没见,太失败了!其实他讲过,经常碰到一群群小朋友见他就喊“好”,听到这些稚嫩清脆的声音,心里甜滋滋的。在锣鼓喧天、叫嚣震地的年头,他遭到伤害,三毛亦在劫难逃,忽一日,《红小兵》上登了他画的《东郭先生》,小友们巴掌拍疼了,天大喜讯,他被上头“解放”啦!新时期,憨态的三毛又到处俏皮活跃,让欢喜者为之共鸣。嗨,1985年居然画起三毛“人到老年”而“脑不管用”,“老来天真”而“鸡鸭不分”,看后顿生“天若有情天亦老”之感。后来买到电影《三毛流浪记》录像带,片头有段“老爷爷”影像,多少有些宽慰。及至1990年看到范用先生为所藏旧刊《时代漫画》请作者题词,他仅在毛边纸上颤抖地签了名,我得知他病了,犹如听说壮士断臂似的,揪心之痛。
不久,我随魏绍昌先生去了几次陈伯吹寓所,呵,入门就见隔成客厅的墙板挂了“老爷爷”为贺而作“三毛献寿桃图”,倍感亲切,有次出门就与魏老提及,想不到魏老说,“张乐平!我太熟。伊的小人都叫我娘舅。”一路上听念叨“融融、慰军”种种好事。(过了几年,有缘魏老赐我一册香港版大著,系慰军先生制作,那封面装帧颇有乃父之作派;又数年,有幸请教融融老师。——昆仲皆精于民国漫画史,为我所佩服的专家。)我请他带我去晋谒,他爽快地答应,并称自己好久没去探望了。就这样,有次顺道领我到了华东医院,出电梯就见“三毛示意安静图”,进得病房只见他正躺着,睁大眼睛望着天花板,似有微茫心事。我仿佛眼前浮现罗丹雕塑《思想者》、耳边回旋马斯奈小提琴曲《沉思》,些许惊觉而顿感:“老爷爷”这般深沉!没多时,便读到应范泉主编《文化老人话人生》约请而写的文章,他云:“因病住院,周围一片白色世界,躺在床上总有几分黯然;闭上眼睛,思绪纷乱,再也触不到我健康时的那根幽默神经。”他放不下手中的笔,其苦痛在于想画而无法画!我想是的。
“老爷爷”画三毛何以老中青幼诵读不弃?他答:“没啥诀窍,就是有一点,我爱孩子。”他不奢谈思想意义,只说“三毛的问题既然如此的多,因此我觉得画不完,写不尽”,“但此问题责任不在三毛本人。我天天画三毛,天天发现三毛的顽劣缺点,因此盼望三毛的生活环境能改善的心情也特别殷切”;他不空论反映生活,仅说“画三毛就等于画我自己”;他不泛言艺术创新,而说“当然是一个冒险的尝试!我想尽可能减少借助文字的帮助,要让读者从我的画笔带来的线条去知道他所要知道的”。实在高明!理所当然地成就笔下这位体弱瘦小、瘪嘴、塌鼻子、冲额角、大光头上添了三根毫发,时而蜷翘、时而耷拉地演绎悲苦欢乐。由此家喻户晓,经久不衰,成了雅俗共赏、最具影响力的畅销读物,乃经典杰作也。
当年三毛出道,遂引得市民动容,排队买报看,挤在报栏前看,都在关怀“小瘪三”的处境,据说还送衣物玩具,连画里三毛打破花瓶遭店主毒打,有人送来花瓶要他转交店主,好饶过三毛。在读者心目里,就是生活中的一位真实孩子,让人得其善、得其乐、得其悲、得其怒、得其怨,搞得“老爷爷”应接不暇,几许高兴几许愁。解放后,百姓盼着续画三毛,可有些议论,弄得他睡不着觉,只得鼓足勇气去找夏衍,夏衍鼓励他再版集子并为序,使他颇有起死回生之感,画了《三毛翻身记》却平添拔剑茫然之绪:“报社给了我鼓励,但同时又给了我在题材上的种种约束,要我结合每一个政治运动来画,如土地改革,反对美帝武装日本,以及镇压反革命等……结果弄得三毛很神秘,当然没有画好。”“实在弄得无可适从,结果只觉得很自卑。久而久之,自己也给自己加上一套清规戒律,更大大削弱了创作的勇气。”在那样一个风雨交加、浮沉颠簸的环境里,他还是自觉存有一份可贵的清醒。
近年来不断观赏到漫画界各路好汉绘制“老爷爷”与小三毛漫像,有老友们的手笔又有忘年交们的“起哄”,各自出奇制胜地寥寥数笔勾勒出一老一小的亲密情态,如方成描绘他这位“老将军”携三毛驰骋之豪气、还有詹同、阿达画的,文心之细,幽默独到,流溢出充满生命感的火花,让人一见就会忍俊不禁。如是,我一直盘算着准备把这些作品汇编成精致的集子,因为我估计他自己看后一定会乐滋滋地夸道:“灵光咯!有趣咯!”听说他托过黄苗子帮助题签“朋友们画我”,可知他曾经也有打算。
二
如我口口声声“老爷爷”,并不妨碍他的大师桂冠。叶冈先生评说:“张氏笔墨的成就,在中国漫画界是数一数二的。”我这个外行浅见,为“上漫”“时漫”“抗漫”所绘封面,《大饭店》、《小都会》、《抢修赣南机场》,解放后《妈妈安心去生产》《南京街头》《百喻经新释》《七十二家房客》,还有晚年所作国画,皆是精品;而私意心得,通常讲到他必话三毛,三毛无疑高峰之作,但不能忽视其都市题材漫画。我杂读成性,从前热衷于看旧报刊,我发现他笔下有很多十里洋场风情,太厉害了!无论题材专注度、作品数量,还有影响力,可谓独树一帜。近年印行的《上海Memory:张乐平画笔下的三十年代》,这本书恰是我曾经的理想,尤为欣慰。书中集中展示此类作品,从文化史研究来看,显示出超强的美学欣赏价值和纪实性质的艺术功能,“老爷爷”其人其作作为个体存在,无疑融入“海派文化”。
“海派文化”是上世纪初以降上海一带为主体的文化现象,在中西新旧思想文艺、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格局、华洋杂处生活方式诸因素交融和冲突过程中,在文学、美术、音乐、戏曲、建筑、时尚等审美领域中产生的综合形态,兼具时代烙印和地方性格。上海也成为文化交流相当活跃的码头,为一批具有现代创作意识的都市“艺青范儿”提供了厚实的经验。他们尝试五光十色、光怪陆离的构图影调,探索街市弄堂、石库门亭子间的质感层次,1920年代末期现代都市漫画应运而生,至1930年代初期形成了漫画创作群体,他不仅投入其间,而且在百花斗艳、群雄逐鹿格局中脱颖而出,自成一格,成为功勋卓著的一员大将。
想当年,他在上海屋檐下绘声绘色繁华时髦、市井习俗、炎凉世态,目击十字街头新生意经、维纳斯夜市之素描景象;描写弄堂百姓隔房观火、三种阶级搬场之幽默画;透视万花筒般老城隍庙、今之博士多矣之剖解图;描画马路职场发财架子、怪病妙方之商品老门槛;写照茶余饭后民谣笑料、舞池中搂抱三分钟之摩登速写。我从中读出了智慧、情绪和更深的东西,也读出在史书专著中所得不到的知识。如《夏夜的上海人》,以传统绘画技法又吸收西方美术技巧,多层次地对旧上海历史提供一种特殊观察角度。可以说,如果没在这个热闹城市里浸泡过,绝不会有如此意识和格调。然他一如“海派文化”特征那样,无门无派又自在得多。在创作中不断嗅出时事脉搏、社会变革的气息,用生活经验及美学意识探究城市环境,以知根知底的笔调来诠释构成各阶层,尤其中产阶级及低层居民日常细节与图景。从描绘社会环境来看,由官场商场到家庭,既有“冒险家乐园”,黑恶势力鱼肉小民,又有“鸽笼”的人情百态;从塑造人物形象来看,上至官僚政客、富商买办,下至小贩游民、淑女姨娘,还有各行各业由外埠人担当的情形,画得精确传神,活灵活现,逐步确立都市情调和现代色彩的风格。再说“海派文化”近商,当年漫画、风俗画这类“闲书”,大量涌现于文化消费市场。他的这类作品可读性极强,名重一时,必定受到“四马路”的追捧,加速了其创作产量。而他并不把自己的画作仅仅看成是供读者消闲遣闷的商品,这样更加成就了他为艺术而艺术的旺盛时期。
值得关注的还有他为海上现代都市文学作品所作的一系列插图,包括绘画书籍封面,同样以当时最时尚的现代派实验技巧为手段,表现城市生活节奏与情感,极有穿透力地刻划世态风尚,揭示小说人物的状态性格和精神现象,成了一位都市风景线的描绘“能手”或“圣手”。可惜抗战军兴,整个上海社会改变了,“海派文化”紧急刹车,他带着画笔从戎去了,现代都市漫画也告一段落。
三
大师乎,其心灵品格因为有爱——我深信。“老爷爷”乐意为小人画画,又常戴红领巾,牵着孩子们的小手,像老母鸡领了一群叽叽喳喳的小鸡在玩耍。他对“文革”瘀伤若无其事,可有件事却耿耿于怀:当他被扣上莫须有罪名,心里好难过,实在憋得慌,就独自走出弄堂口,墙上糊满了批判他的大字报,只见一群小朋友过来,对他喊“一、二、三”,他感到奇怪,难道还会向他问好,便乐滋滋地继续听下去,听到的却是“打倒张乐平!”使他“像兜头一盆凉水,心直颤抖”;他还看到老师带一群幼儿园孩子在唱《我爱北京天安门》,就情不自禁坐到椅子上和他们一起唱起来。孩子们爬到他身上,有的拉他头发,有的摸他脸,心里乐开了花。此时一个过路人认出了他,去和老师说了,老师慌忙把孩子全带走了,“我恋恋不舍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眼泪不禁簌簌而下。”看似涓滴动情之计较,确实大爱之怀。
在我浏览其战时作品、解放后的文稿,则会感受温和尔雅之中蕴含耿介刚直,一面爱得柔情似水,一面恨得金刚怒目。当年他是抗日战士,漫画将军!当其仍沉浸在描绘上海滩众生相还意犹未尽时,日寇魔爪伸向吾国,他画了《窘》:窈窕淑女惊呼自己艳丽旗袍被战争的铁丝网刺撕破。神来之笔,极富感染力;还有《当他们很天真地做着抢位置的游戏时》,颇有异曲同工之深刻;又在《人言》周刊发表《对内与对外》。读着这样“超越形势”的作品,其创作时的情绪和体温,跃然纸面,笔墨也就日趋凝重严峻了。抗战爆发他出任“漫宣队”副领队,在我眼里相当“二万五千里”长征,下笔挥洒好比刺刀,如《武汉的神经麻木症》《王八别传》,一发不可收,直到最后,孤军奋战;胜利后的《自由言论?》、《不平衡的平衡》,毫不掩饰地直抒胸臆。我总想那时他不知何等风采,毕竟太久远了。谁知近年从《三毛之父“从军”记》等书中,一睹英华,如我在其晚年见到的那般深沉。我在选编《抗战漫画》时,屡次三番被他宏大墨彩所感动,第九期封面以其特有灵感表达了爱憎激情。我特地精细扫描提供制作书封,却被用作封底,引为恨事。
友人说乐平兄胆子特别之小,我以为搞错了,实在小看其内敛慎重。走过战争,照旧用图画宣泄心中块垒,1946年在文汇报馆会上忿然道:漫宣队“危急时,高唱军政自顾不暇而置之不理,而到不需要时,就一脚踢开,不管你流落他方,生死存亡。”“看到这种不负责任、心血来潮、颐指如意的作风,展望今后的所谓复员工作,怎禁得住不为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存亡担忧。”此番话酣畅淋漓,亦可说“痛快”,其胆量不算小吧,已大至“包天”矣。1957年是个啥辰光?竟于《文汇报》“发牢骚”:“实行了办公制,每天慌着准时签到,而且会议实在多,我又生怕人家加上‘不积极’的帽子,所以总是每会必到。这样‘积极’是‘积极’了,但是画却没有了。”颇有振聋发聩之势,骨子里相当硬气倔强,即使“文革”后期,非但没患“缺钙”症,如遇心中不平,全然不顾所谓“解放”处境。有次与几位“臭老九”在芦芒家喝酒,当聊到“猫论”时,没见小心翼翼,当场挥毫《黑猫》;生前最后漫画《猫哺鼠》,有力地抨击腐败现象。1987年儿童节,杂志编辑请“老爷爷”贺节,他先客气道:“说什么好呢?有点踌躇,怕讲出来不那么切合实际。”话锋一转便推心置腹地提醒“不要到‘六一’才想到儿童”,他太熟悉独生子女的种种情形了,很有发言权,更不怕被斥“唱反调”。
他人缘好,口碑佳,然“无奈”之时也会不惜得罪同道。1935年为创作寄居某俱乐部,有感而漫画:老板用绳捆住三位工人的脚,依次放入崖下取钱,再依次往上递给老板;钱到手后,老板剪断绳子,工人掉入深渊。想不到这幅画会使一位有钱同行拍桌子,指责挑拨劳资关系。他义无反顾。后来还有代孩子们请命之作《叔叔,请别忘了我们》,吁请同道兼顾儿童作品。晚年病重仍作画“救灾义卖”。设想,如果画家不关心社会现实,无自觉的爱恨交织的精神追求,作品也就缺少生命体验和情感良知。其画之所以撩人,是由于呼唤人道尊严,核心内容充满人道精神,当祖国存亡关头,会挺身而出;当社会不公、民众苦难,会仗义执言。——正是无私无畏的胸襟和胆魄,乃大勇者。
四
抒发如上“痴迷”种种,这样的甜蜜伴随我成长而一直藏于心间,倘若得闲照旧“穷追不舍”的话,还是想再回味他老人家的趣事。
近年时兴“怀旧”,老照片流芳后世,我居然受益,在图书上读到好几帧“老爷爷”的旧照像,很让我欣赏的是老人家年轻时长相“挺括”,发型特别清爽茂密。我观海派笑星垂头展示发型:“头丝清爽伐?”捧腹笑过,不禁想起他晚年躺在病床上银发依然浓茂考究,头丝当然煞清。从前特伟老人告诉我,小丁年轻时总爱穿洁白袜子,顶时髦。可我北上京城,却听见丁聪老人连连自愧弗如:“小阿弟侬嫩了,伊自家和乐平兄的‘奶油包头’最挺括!”再看照像上“老爷爷”的“大包头”“小分头”,张张头丝锃亮,尤其头戴礼帽身着风衣的风度,绝对“老克勒”!如今怀旧影剧里的人要么“前卫”“先锋”得邋里邋遢,要么头发少来兮,何能攀比呢?可他谦虚地让笔下“小瘪三”仅留三根毛。如今市面上有“搞笑”之言:“‘低调’就是‘腔调’”,看看他的画,只觉得清逸素雅,除大幅宣传画,大都貌似“无技巧”而蕴藉技巧之精髓,创造了独特视觉语言,慢慢渗透,生动感人,假是画小动物也情趣可爱,是一位把技法“低调”发挥极致的大师。我见过他几幅自画像,时代印痕清晰,均无“高大全”似的自我表现,赋予亲和力。1939年与1941年的,明显记录了生活情感变化;而1966年的,画出了迷惘困惑之神态;丁聪赞语:“我佩服他的画构思巧、技巧高,可他从来不以此傲人。”一语破的,道出真实。还听前辈讲他画画得意时,连大拇指也翘得恰到好处,最多糯语一声“邪气崭咯”。我有时心气过躁,就想翻阅图书上他的照像,慈眉善目样子皆“乐”而“平”之面貌,看去厚道极了,真有消气解躁功效。听了他很多温良恭俭让的故事,想来正是照像上的从容不迫之风范,假如编印一册他的老照片,多有意思呵。
好酒善饮,是他朴素生活中的唯一嗜好,而又多趣事,特别“好白相”。传言幼时醉倒在他老爸的大酒缸边上,还听讲“文革”“张乐平不许喝酒”的标语一直贴到他屋里,仍旧“恶习难改”,甚至写检查时还要把藏着的酒拿出来过瘾。我看到江帆漫画“三毛发现老爷爷把酒藏在后腰的秘密”、田原漫画“三毛规劝图:张爷爷你再喝酒,我就不同你玩了!”听说他一面不好意思一面又频频举杯:“好哩好哩,戒酒戒酒。来,为我戒酒,干杯!”此嗜好之于他是“神仙乐”,可我更愿意想象那是催生艺术灵感之尤物。他善饮绝非闹中取乐,习惯“打老虎”(自斟自酌)地进入“腾云驾雾”之境,我猜测,这是把心灵置于醇酒佳酿里品尝思想。据说往往是老酒一杯后,创作思维得以兴奋,出笔之准如有神助,简直精彩极了。而酒后最具特色的是恳切地冷面“戏话”,是出了名的。1990年代后期在锦江饭店听殷振家先生讲“抗战艺坛趣话”:黄永玉用烂泥加蛋清为他做了漫像,乐平兄看到后一脸正经地开起玩笑,让他在近一个甲子里,每每想起就笑得够呛。
他还有个温暖之家,我以为是他跨过坎坷征服磨难的奥秘。1945年《携家流徙图》,自画上饶沦陷后提行李带妻孩漂泊情形。当初在旧刊上读到,霎时闪念:多么温暖的家庭!画上看似平步青云,实在异常苦矣,有人亲眼看见他摆地摊卖随身衣物,打着赤脚卖皮鞋。世事多艰,正是温暖家庭支撑他把日子过得滋味,我看到1959年他的“全家福”,遂形容为“鸟巢”。从前听魏绍昌老人说,他夫人是上海滩大律师的千金,婚前是其读者,在抗战中演剧队大名角与漫宣队大画家喜结伉俪;他儿子一不小心也泄漏天机:母亲是父亲最有力的支持者,很多事情帮父亲抵挡着。他们夫妇还收养好几个“编外”儿女,帮助度过困难岁月,家庭规模更庞大;试想养家糊口多么艰辛,便可明白这俩位家长的博爱胸怀。“文革”他是全市批斗的“通用票证”,有时上午在杨树浦被斗,下午又赴曹家渡游斗,晚上加场到徐家汇陪斗,他却自嘲:“终朝碌碌,像跑场赶集市,回到报社被监督劳动扫厕所。”如此能从迫害中很快恢复过来,我想,就因有个能小憩的舒服“鸟巢”吧,这让我不禁想起还有一幅1969年他与四个儿子的合影,让我震惊了半晌,感受超常的温暖和力量,我称其为非常年代的“五君子图”。
如今重温“老爷爷”其人其作中有爱有恨的滴答往事,能体会他思想的敏锐和深刻的现实关怀,可见爱憎分明的品质贯穿了他的伟大一生。连日本森哲郎都尊道:“伟大的人民漫画家张乐平先生,有一天我将会执笔写出这位值得中国人民自豪的伟大漫画家的故事。”这是颇有启示意义的话,让我省悟,“老爷爷”这顶“大师”桂冠具有“人民性”。所以,我敲击键盘录下私意,实在是为了:“感念您,人民的大师‘三毛老爷爷’!”
——摘自2011年第2期《万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