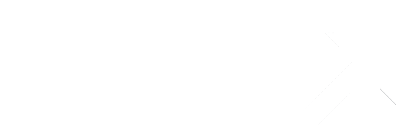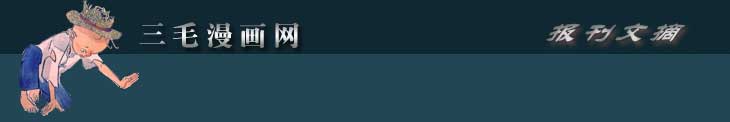
张乐平伯伯和我
王龙基
今年11月10日是张乐平伯伯百岁华诞的日子,虽然张伯伯离开我们已经十八年了,但乐平伯伯的英容笑貌依然在我眼前耳边。伯伯所塑造的不朽的儿童形象“三毛”深入人心、家喻户晓;伯伯一生所追求、所期盼的“儿童乐园”——所有的儿童都有饭吃、有衣穿、有书读,在如今早已变成现实。随着时间的延续,我们对张伯伯的思念与日俱增……
因为有幸扮演电影《三毛流浪记》中的三毛一角,乐平伯伯和我父子般的友情超过了半个世纪。解放前因生活贫寒他患过肺结核,解放后治愈了。“文革”后,老病根逐渐成了肺气肿,加上糖尿病,身体每况愈下,本来红润的脸逐渐消瘦。我经常去看望他。乐平伯伯全家九口人,伯母姓冯名雏音,尽管因严重糖尿病人过分肥胖,但她十分能干,思路敏捷,条理清楚,乐平伯伯的大小事情全由她安排。在她枕头下放着三个笔记本,一个记事,另两本分别记市内外通讯地址,把伯伯的衣食住行及社会活动安排纪录得井井有条。伯母每次见到我总喜欢说:“这么多年了,龙基总来看望我们,就像是我们自己的孩子。”
乐平伯伯一共有七个子女:大女儿娓娓,小名咪咪;二女儿晓晓,小名小小;老三是儿子融融,因为长得虎背熊腰,所以小名叫熊熊;老四是女儿,因为嫌生的多了,便取名朵朵,小名多多。当时是人多热气高的时代,所以多多后面又多了三个弟弟建军、苏军、慰军。因为娓娓比我小一岁,所以小时候,他们都叫我三毛哥哥。
乐平伯伯去世后,他的子女们将伯伯七十多年来在各地报刊杂志上所发表的漫画都分别整理成册,并将《三毛流浪记》、《三毛从军记》等作品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和各种不同的文字出版发行,受到全世界儿童的喜爱。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有关三毛的连环画始终能保持畅销。
这些年来,伯伯的子女们每年春节都要聚在一起吃一顿全家团圆饭,包括我们夫妇和编外儿女们,大家尽管都已六七十岁了,但在一起的欢快和友爱、兄弟姐妹的手足之情如同当年。
1948年至1949年(本网注:应该为1949年),在我从试镜到拍电影《三毛流浪记》的整个过程中,乐平伯伯都常和我在一起,他还不时送我他画的三毛漫画。他曾多次给我讲述他画流浪儿三毛的最初冲动:那是在1947年初的一个寒冷的夜晚,刺骨的北风呼呼地吹,夹着鹅毛大雪把上海染成一片银色,屋顶上积着厚厚的雪,树上挂满银白的雪,马路已经被茫茫冰雪所罩,分不出车人行道。乐平伯伯在一条弄堂口,看到三个10岁左右的流浪儿。他们用破麻袋紧裹着身体,赤着一双脚,紧紧围抱着一只白天烘山芋的炉子,他们不停地踏着脚,鼓着冻红的腮帮吹着即将熄灭的火,一个劲地吹呀吹呀,就靠那一点儿火星取暖。乐平伯伯是没有能力帮助他们的,那时这种景象比比皆是;那时,伯伯居住在嘉兴,到上海是借住在他堂弟家。第二天一早,他又走过那条弄堂,他看见两具已经冻僵了的小尸体依然伏在炉旁,他们的小手还伸在早已熄灭的炉壁里……乐平伯伯久久地站立在那里,望着那凄凉的景象,他的脑海中显现出三毛的形象。就这样,他开始了《三毛流浪记》的创作,在上海《大公报》上连载。每次乐平伯伯总是含着泪讲述,我总是流着泪听。
阳翰笙伯伯在1948年将《三毛流浪记》改变成电影文学剧本后,因时局关系就撤离了上海;陈伯尘伯伯代为修改一遍后又匆匆离沪。后来由李天济叔叔修改定稿。乐平伯伯很赞赏这个电影剧本。
本来计划由陈鲤庭伯伯担任这部电影的导演,因为当时他执导的电影《丽人行》还没有停机,还因他自己感觉对儿童影片不十分熟悉,所以就请当时他的助手赵明和刚从演剧队来的严恭两位青年担任导演。
鲤庭伯伯把寻找三毛演员的任务交给严恭,他一连找了几个月也没有结果。其中有一次,别人介绍他去看演员,他走进一幢洋房,只见一桌丰盛的菜肴,一个老板和几房太太领出一个胖小子要扮演三毛,吓得他连饭都没有吃就走掉了。
一天严恭叔叔路过昆仑电影公司门口,看见我和两个大孩子趴在地上打弹子。当时我才8岁,刚拍完石挥叔导演的电影《母亲》,母亲由秦怡阿姨扮演,我演他儿子。偏偏打弹子我赢了,而两个大孩子欺负我小,输了不给我弹子。我急了,不管自己势单力薄,论理不成便抡起拳头就打,结果是我一个小的战胜了两个大的孩子,把弹子拿到了手。这引起了严恭叔叔的兴趣,他细看我大脑门、细细的脖子、大眼睛,加上那股倔犟的劲头,真有几分像漫画上的三毛。
为了让当时昆仑公司艺委会的阳翰笙、郑君里、陈鲤庭、史东山、蔡楚生、沈浮伯伯们审定,赵明和严恭叔叔想让我外形更贴近人物,便给我剃光了头发。开始我死活不干,两位叔叔好说歹说我才勉强剃了。他们按图索骥——按漫画三毛的造型给我化妆,让我披着破麻袋,赤着双脚,污着脸试镜头。
想不到,试片放映了二遍后,所有的伯伯叔叔,包括电影公司老板都认可了:“这就是三毛!”乐平伯伯高兴地讲:“这就是我想象中的三毛形象。”
小时候我非常喜欢看漫画《三毛流浪记》,十分同情三毛的遭遇,更喜爱他那正直善良、倔强机智、活泼聪明的性格。,而且我也有许多类似三毛的苦难经历。我知道饿得吐青黄水(胆汁)的滋味,睡过稻草当垫被的床铺,小时候父母也曾准备把我送给别人……所以在我参加拍摄的十余部电影中,最喜欢三毛这个角色。拍《三毛流浪记》时,我感到像在生活中一样,一点也不陌生。三毛是旧中国千千万万穷苦儿童的典型、缩影,其中也有我的影子,我觉得三毛是我,我就是三毛。
电影开拍前我就和赵明、严恭叔叔一起住到中电二厂(现大木桥)一间不大的房间里。因为我小时候十分顽皮,又不容易受拘束,所以我们还签订了一份“合同”,他们一本正经地签名盖章,而我当时没有图章就就签名按了手印,约法三章,约束我按时作息,遵纪守法,认真专注地进行拍摄工作,“合同”就贴在我床边的墙壁上。乐平伯伯经常在那间小屋给我讲他的漫画三毛的故事。
赵明叔叔1960年担任上海电影专科学校副校长,兼导演系主任,我在电影文学系读书,成了他的学生。他对我讲,拍三毛时想不到那个“合同”还真起作用,而且合作的很好,基本上没有出过什么问题。当然,偶然的例外也在所难免。严恭叔叔前些年就告诉过我,有一次,摄影棚都已经做好一切准备,摆好了镜头位置,布好光,准备开拍了,我却不见了。急得在场的人都团团转,到处找我,好不容易在场地的一个角落,看见我一门心思在寻找什么。那时我最喜欢的玩具之一是自己用火柴盒做的汽车、沙发。我用了七个空火柴盒子做了一个写字桌,藏在那里,那天突然找不到了,我正在发急。赵明叔叔马上叫人买了一大包火柴给我,我把火柴统统倒掉,拿着一包空火柴盒子,就高高兴兴地去拍戏了。一边拍戏,一边我还和他们去外滩排污沟旁看流浪儿的“寓所”,到苏州河畔和小乞丐一起搬运粮车,一道抢饭店拿出来的剩饭,并和许多流浪儿童交了朋友,我熟悉了他们的苦难身世和辛酸经历,我同情他们,也更热爱他们了。我在肇家浜河畔看到过船民那连狗都不如的生活,我忘不了有多少人是住在用废旧自行车钢圈搭起来的“滚地龙”里,“房”不足自行车的钢圈高(因为一半是埋在地里当墙基),睡觉时得钻进钻出。
为了像三毛一样赤脚走路,开始我是穿着袜子走,电影正式开拍后我已习惯光着脚满地跑了。在拍电影过程中,我一直是赤脚生活的。记得电影拍完后,妈妈爸爸特意给我买了一双新皮鞋,可我就是不肯穿,还是赤脚舒服,自由自在。
在拍三毛喝浆糊一场戏时,乐平伯伯画的三毛喝浆糊后来肚子痛的漫画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所以尽管我知道给我喝的是藕粉,可真要我捧起又脏又破的浆糊桶喝,我是不肯的,怕肚子痛。于是导演带头先喝,我才试着用嘴抿一抿,实在不像饿慌了的样子。中午,讲好不给我吃午饭,下午要我进摄影棚自己找东西吃,于是就出现了小三毛抢浆糊桶猛喝的镜头。等镜头拍完了,他们也没能从我手上把浆糊桶抢下来,因为加糖的藕粉太好喝了。
三毛的造型是按照乐平伯伯漫画设计的,那蒜头似的圆鼻子是用泡泡糖做的。而那三根毛,其实是用外面粘着毛绒的三根铜丝贴在橡皮膏上,然后再贴到我的光头上造成的“三撮毛”。为了贴住这三根毛,化妆师辛汉文伯伯每天总是亲自给我剃头,还要用剃刀刮头,那把剃刀在我头顶心上来回刮,我实在吃不消了,头来回扭动,他用手打了一下我的头,顺口道:“小赤佬,头勿要乱动!”我本来就不情愿,便立即回过头顶了一句:“你是——老赤佬!”结果双方很认真地大吵了一场。当时的情形,便在电影中再现了出来,就是三毛被富人买去当义子,领着流浪儿们大闹命名宴会后,三毛和贵妇对吵的场面和对话。
电影《三毛流浪记》的场景,大约四分之三是在实地现场拍摄的。在人群熙熙攘攘的外滩,流浪儿有的奔跑着卖报,有的再捡香烟头;在四川北路桥头,流浪儿争抢着推三轮车上坡过桥,向坐车人讨几个小钱;风雪严寒的冬天,树都包上了稻草,而衣不蔽体、饥寒交迫的流浪儿们,夜晚无家可归。天天都有冻死、饿死、病死的孩子……这一场场、一幕幕活生生的景象和漫画融为一体,在我眼中、在银幕上、在拍摄过程里,我对当时不公平的黑暗世界,产生了和三毛一样的不满情绪,播下了与三毛一样反抗的种子。
在电影中有一场“豪门大宴会”的戏,布置富丽,场面豪华,其实那并不是实景,而是在中电二厂摄影棚里搭的布景。顶是一个玲珑的小模型,通过摄影技术把小顶和大厅衔接成一个完美的整体。
众多男女贵宾都是著名的大明星客串演出,这在中国电影史上是空前的。因为场面宏大,一连拍了一个星期,每天为接送全体女明星到美发厅做头发,就用了五辆轿车。这些大明星中有上官云珠和她的女儿姚姚、中叔皇、王静安、朱莎、朱琳、沙莉、林子丹、金淑之、吴菌、林默予、奇梦石、徐曼、徐缓、袁蓉、孙道临、高正、郭玲、黄温如、梁明、许兰、章曼蘋、张邵、张婉、张逸生、傅惠珍、张庆芬、程梦莲、农中南、汪漪、熊伟、苏英、苏茵、苏曼意、谭云等阿姨叔叔们。
其中还有沈浮、高依云,应云卫、程梦莲,魏鹤龄、袁蓉,项堃、阮斐和新婚不久的赵丹、黄宗英,凌之浩、沙莉,刁光覃、朱琳共七对夫妇参加。
参加宴会的服饰都是个人自己设计的新奇时装,显示出当年的穷奢豪华气象。
扮演小学看门人的是刁光覃,警察是石炎,小老大是丁然,爷叔是关宏达,阿姨是黄晨,贵夫是杜雷,贵妇是林榛,男仆薛敏,家庭教师莫愁,瘌痢头是孟树范,小牛是王公序,老乐师是我爸爸王云阶。
在电影拍摄过程中,乐平伯伯经常在摄影棚,时而是名观众,默默站立在一旁观看,时而又是一位编导,在现场指导启发。其中许多时光是和我一起度过的。当时的电影杂谈《青春电影》记者给我拍照时,就是乐平伯伯陪伴着我,一起选了一堆圆木做背景,拍了不少照片。他还把自己的一顶法兰西帽给我戴。那张照片成了《青春电影》的封面。
1949年9月,当上海六大电影院同时上映《三毛流浪记》时,发起了义卖活动,乐平伯伯画了六幅三毛漫画印成贺卡,我和大明星们一起在电影院门口签名义卖。
1958年和1980年,全国两次重新拷贝发行电影《三毛流浪记》,不久香港和东南亚将电影译成粤语片,收到很好效果,乐平伯伯十分高兴。1981年,我带小儿子王旻淦去看望伯伯,他望着旻淦笑眯眯地对我讲:“长得太象你小时候了。”他把刚再版的《三毛流浪记》、《三毛从军记》送给我,还不顾手指颤抖,花了许多时间画了一幅彩色三毛送给我,题为:“龙基弟留念辛酉年初夏张乐平画”,还盖了一颗红印章。这幅画我托人裱好一直挂在家中墙上。
特别令乐平伯伯兴奋的是,当他从国外记者口中知道1981年5月21日至22日,在戛纳电影节期间举办了中国电影日,放映了《三毛流浪记》等四部电影后,巴黎六家电影院继续放映《三毛流浪记》,连演六十天,接着8月份两家影院又上演了一个月。《三毛流浪记》轰动了巴黎,电视台播放了预告片,巴黎的餐馆、咖啡馆前张贴了大幅海报。影片受到了法国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各家报刊纷纷刊登介绍文章和影评,称“影片堪与卓别林的《寻子遇仙记》或布努埃尔的《被遗忘的人》相媲美”。乐平伯伯还拉着我和港台记者一起在大海报下合影。这部电影还获得1983年葡萄牙第12届菲格拉达福资国际电影节评委奖,1984年意大利第14届福尼国际青少年电影节荣誉奖,2005年纪念中国电影诞辰100周年,评为“中国电影百年百部经典银幕形象”之一,“我最喜爱的百部中国电影”之一,并于2009年9月9日第十届中国国际儿童电影节上荣获“建国六十周年儿童电影经典形象奖”。
1982年,乐平伯伯邀请我出席在上海美术馆举办的“张乐平美术作品展”的开幕式。我和伯伯、伯母一起仔细欣赏全部作品,乐平伯伯还不时告诉我作品的构思和意图。当时乐平伯伯已年过七十,可那精神、那风貌似同青年。
1985年在上海市少年宫,我和乐平伯伯谈起往事,谈到漫画和电影的再版、重映和评论,听了著名动画艺术家阿达谈连续动画片《三毛流浪记》各集的设想和构思。可惜时隔不久,突然听到阿达因病离开我们的消息,乐平伯伯和我都为失去这样一位大师和挚友而悲痛。于是那部动画片成为了永远没有完结的作品。
20世纪90年代初的几年,乐平伯伯总有一半时间要在华东医院度过,我经常看望他老人家。一次我去病房,见床空着,我便一间一间寻找过去,他穿着病号服,坐在一把藤椅上,双手托着头全神贯注地看着电视新闻。我站在旁边凝望很久,他那神态,不像是一位老者,而像一个天真儿童。
1987年的春天,乐平伯伯兴致很高地让我扶着他从华东医院的一楼走到四楼,他把挂在每层楼梯口,他画的三毛漫画指给我看,告诉我每张画的神态区别。他最满意二楼那张,于是拉着我在那张画前合了影。
在我的日记本里,还保存着乐平伯伯画的两个三毛头像。那天,他刚喝过二两白酒,心情很好,他随手拿过一张纸,教我怎样画三毛的轮廓,三根毛应该如何用笔,着力点在什么地方。他一边在纸上画一边对我说:“龙基,你不要看三毛就这么几笔几划,其实每一笔、每一划都充满了三毛的喜怒哀乐。”画着画着他手又抖了起来,他对我说,等他手好一些,画一张我的肖像素描。后来他又提过很多次,总因手抖没有如愿。1991年底我去医院看望伯伯时,他还没有忘记这件事,他对我说:“过几天我身体好些,回家去住,我给你画肖像。”
张伯伯赠给我的彩色水彩三毛,我将高高地挂在我的书房;张伯伯的漫画图书,我将会很好珍藏并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张伯伯虽然离我们而去,去到他向往的漫画世界,去到他追求的“儿童乐园”,去到他一生执着追求的艺术殿堂……他留给我们的无价财富、中国的漫画经典,几代人喜闻乐见的“三毛”,将永远活跃在亿万中国人的心中。
——摘自《档案春秋》2010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