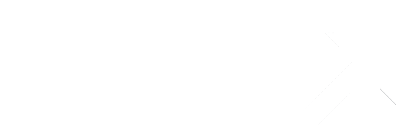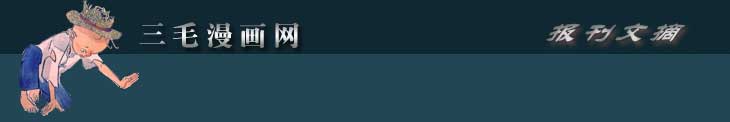
“姑婆”华君武──张慰军回忆父亲张乐平和华君武的交往
詹 胜
今年十一月是已故漫画大师、“三毛之父”张乐平诞辰一百周年。
今年六月,另一位漫画大师华君武仙逝,中国又少了一个漫画泰斗级人物。华老和张老是老朋友了。为此,记者采访了张乐平的小儿子张慰军。
记者(以下简称记):我看见报道,说你在漫画大师华君武去世后特意代表全家去北京参加了家属告别仪式,请你说说你父亲和华老的交往好吗?另外,据我知道,你父亲比华老年纪大,为什么你叫他伯伯?
张慰军(以下简称张):是的,华伯伯比我父亲小五岁,不过我和我的哥哥姐姐都从小叫他华伯伯。他几次要我们改口叫叔叔,改不过来,已经习惯了。
告别的那天(二○一○年六月十八日)在北京友谊医院,看着鲜花丛中盖着党旗的华伯伯是那样的安详,我也只能默默地再叫一声华伯伯,说一句:华伯伯你一路走好!
我父亲和华伯伯相识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那时候他们都很年轻,都是漫画作者,都去漫画会和漫画界前辈丁悚家。以至於他们和那个年代的几个漫画家都要调侃差不多年纪、老实巴交的小丁——就是丁聪——叔叔:“阿拉迭格辰光全是去寻倷爷,是倷爷格朋友,所以侬要叫阿拉爷叔……(我们那时候都是去找你父亲的,是你父亲的朋友,所以你应该叫我们叔叔——记者注)”
记:那时候有“三毛”了吗?
张:“三毛”是一九三五年创作的,我估计他们认识的时候还没有。我父亲那时候已经是专职画画了。华伯伯好像先是在读大学,后又在一家银行工作,以画大场面的漫画出名。
记:哦,那到张老去世,他俩一直交往了有六十年左右。
张:中断过两次,一次是抗日战争开始后到解放,有十多年;另一次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近八九年吧。
记:抗日战争时,他们分别在解放区和国统区?
张:是。
一九三七年八月“八一三”过后不久,包括我父亲在内的上海七个漫画家成立了抗战漫画宣传队到当时的首都南京宣传抗日,南京沦陷后转到武汉。大概一九三七年底,华伯伯从上海到武汉,和我父亲及他们漫画宣传队的成员匆匆见了一面后就去了延安;我父亲和漫画宣传队南下。一别十多年,到解放后他们才又再见到。
记:中间一点联系都没有?
张:几乎是一点都没有,因为是抗战期间,通讯和交通都极不方便的。到了解放战争,那就更没有联系了,是分别在敌对的两个政党所统治的地区。
在抗日战争期间,他俩在各自所在的地方画了大量的抗日漫画。在解放战争这段时间里,我父亲创作了《三毛从军记》和《三毛流浪记》等等;华伯伯画了这幅(指了指作品)脍炙人口的蒋介石假停战的漫画像,以及非常多和影响深远的作品。不过当时他们都不知道对方的具体情况。
他们的画是不同的风格,不同的表现方法,但是追求正义是一样的。他们再次见面应该是在一九四九年北京文代会期间。
记:以后他们就恢复了交往?
张:对,以后我父亲每年要去北京开会。华伯伯也经常来上海,来了以后就找沈柔坚叔叔、盛伯伯——就是特伟,也是一个比我父亲年纪小,而我们都叫伯伯的长辈─还有我父亲几个在一起谈工作、做美术片造型,华伯伯还写了几个美术片的剧本。
还有,他们在一起就互相开玩笑,一直到很老了还那样。我们在旁边听了也一起笑,现在想想也好笑。
漫画家嘛,幽默是他们的本性。
解放后,有一些比较左的解放区来的干部对当时留在国统区的人很不以为然。不过他们——就是沈叔叔、华伯伯、盛伯伯,还有赖少其伯伯和吕蒙叔叔等等,对我父亲都很好,没有这样的表现。
记:你父亲不也是共产党党员吗?
张:那是以后的事情了,我父亲是“文革”后的一九七九年才入党的,但是他刚解放就打入党报告了。后来政治运动不断,据说我父亲还是内定的右派,所以到粉碎“四人帮”后才被批准。
记:说个题外话,在抗日战争时候你父亲是什么政治观点?有没有想过去延安?
张:(笑)我父母结婚的日子是在一九四一年三月十八日,三月十八日是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成立的日子。你从这点就可以知道我父母那时候的政治观点了。那时候的文艺青年其实有非常多是这样的观点。
皖南事变后,赖少其伯伯从上饶集中营越狱找回新四军的时候遇见我父亲,他和我父亲也是在上海就熟悉了,在事变前还为我父亲的抗日宣传画写过文章。他们约好解放区见——这件事情沈柔坚叔叔也提起过,说那时候他在苏北根据地就听说张乐平要来。
可是后来我父亲被当作人质走不了,因为有特务发现漫画宣传队有一些关於共产主义以及其他的禁书,他们要把全部队员扣留。后来经过交涉,才留下作为队长的我父亲。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
现在回过头看,我父亲没有去解放区有了另外的结果,那就是创作了《三毛从军记》和《三毛流浪记》。
记:好,话说回来了。你对那时候你父亲和华老的交往印象很深吗?
张:他们谈工作什么的我当然不知道,只是估计在谈工作而已,因为那时候我还小。事后知道的。
我开始有印象是在一九六一年秋天,我父亲和盛伯伯、华伯伯等在苏州为了几个动画片搞创作,住了几个星期。我妈妈带我在周末去苏州看望,碰到了华伯伯带来的小儿子方方,就此开始了我们第二代的交往。
从苏州来上海,方方住在我们家。后来大了,来上海出差什么的,方方也经常会在我家住上几天。
七十年代末我借到北京工作过一年,休息日就去华伯伯家住,好像就是周末回家那样。端端大哥对我就像对自己弟弟,伯伯、伯母就更不用说了。
以后都是这样。
记:你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你父亲和华老又中断了联系,那是怎样的事情?
张:一九六六年“文化革命”开始了,我父亲当时在《解放日报》工作,兼任上海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我父亲是上海美术界最早被打倒的。罗列了很多罪名,太多了,我在这里也不说了。
华伯伯在北京也被打倒了,这样一个从延安出来的共产党干部也被打倒。批判他的文章还上了《人民日报》,有大半版面。那时候被党报这样地批判,是表示真正被打倒了。我父亲看了很担心。
但是,他们已经也不再联系了,也不可能联系。
记:联系了是不是罪名更大?
张:是。
记:后来又怎么恢复联系交往的?
张:大概在一九七五年,邓小平恢复工作了,政治气氛相对宽松,他俩也算是被解决问题,可以恢复部分工作。华伯伯写了一封信给我父亲,一是告诉了他自己几年来的情况,二是询问我父亲和很多朋友在“文化大革命”中以及当时的境遇。我记得我父亲很激动,马上读给我母亲听,坐下就写回信。
记:那什么时候又见面的?见面一定很高兴了!
张:见面应该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了,是在北京开会的时候。具体什么会议我忘记了,反正不是政协会议就是文代会。
经过“文革”的苦难,能再次见面,他们当然非常高兴。会议安排有饭吃的,但是华伯伯一定要请我父亲到外面另外吃一顿,顺便还叫上了电影演员赵丹叔叔。三个人一进饭店,服务员就认出了赵丹叔叔,华伯伯又介绍了我父亲。这顿饭吃得非常开心,三个好酒之徒也喝了不少。吃好,华伯伯对赵丹叔叔说:“因为你的脸,服务态度难得见到这麽好;”对我父亲说:“因为知道你是穷孩子三毛的爸爸,今天厨师做的菜又好又多。”赵丹叔叔对我父亲眨眨眼睛,然后两人同声说:“哦——原来今朝迭顿饭是阿拉请侬啊!”(笑)
记:后来就经常见面了吧?
张:每年有几次,譬如政协、文代会、美协会议等等,是我父亲去北京;华伯伯又经常为了工作来上海。一九八五年上海办了《漫画世界》,赵超构伯伯请我父亲当主编,所以他们为了创作也经常见面的。我父亲去世后,《漫画世界》是华伯伯当主编。
我父亲一九九二年去世,华伯伯来信来电话,还写了文章悼念,以及特意赶到海盐参加我父亲纪念馆揭幕仪式等等。
后来好几次我和华伯伯见面,他说他经常会想起我父亲。
他还说他很后悔和我父亲在一起的时候老是开玩笑,没有互相交流创作的体会。因为太熟悉,到我父亲去世后他才想到为什么没有问问我父亲的作品是怎么会受读者这麽欢迎的。
到我父亲去世十多年以后的二○○五年,华伯伯来上海,还在虹桥迎宾馆和我回忆起我父亲。他说:“你妈妈反对你爸爸喝酒,老是争吵;你宋绮阿姨也因为反对我喝酒和我争吵。我和你爸爸私下都说,要一起到山上找个地方躲起来。唉,现在你爸爸不在了,宋绮阿姨也不在了!”
说完他沉默了,我也沉默了。
记:很伤感。
张:是,很伤感。
不过华伯伯很会调节气氛。看我也伤感,就说:“你爸爸叫我姑妈。”说完他像个顽皮的小孩子那样笑了。
记:姑妈?
张:是,姑妈。
那是一九八○年末,中国漫画家代表团访问日本。说是代表团,其实只有四个人:团长是华伯伯,团员就是英韬叔叔和我父亲,还有一位外交官。我父亲刚过七十,身体不太好,一路上都在华伯伯他们的照顾下,据说连口水流下都是华伯伯帮着擦。他们笑说其实真正的团长是张乐平。
去日本之前在北京,黄永玉叔叔塞给我父亲几百美元。这些外币在当时对我父亲来说很珍贵了,他想在回来的时候买个电视机,所以就贴身藏好。华伯伯就一路问钱藏好没有,我父亲就会下意识地摸一下口袋,呵呵。还有,怕我父亲在外贪杯,华伯伯就一直叮嘱,不让我父亲喝酒太多。我父亲嫌他老管着自己,就说“侬烦煞了,姑妈!”
就此,我父亲老远见到华伯伯就叫:“姑妈!”
记:哈哈,那你有叫华老姑婆吗?
张:当然不会叫,也不敢叫。端端、方方和我好像亲兄弟,也许我叫了结局也要像小丁叔叔那样,要我叫他们爷叔了!
——摘自2010年7月28日《大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