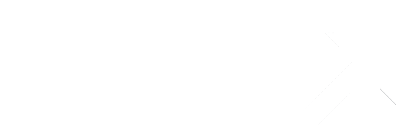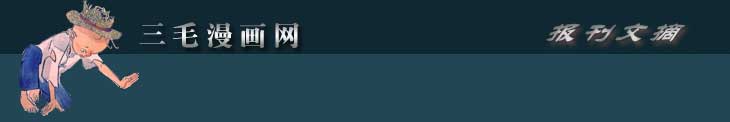
一诺千金,乐平先生为我画三毛
蒋 风
岁月像秋天的落叶一样飘逝,但埋藏在心灵深处的记忆却是永存。30多年前那个深秋,1978年10月11日至21日那10个日日夜夜,在江西庐山参加全国少年儿童出版工作座谈会时,与新老朋友相聚的情景又从记忆深处,像放电影似地浮现出来。尤其令我难忘的是张乐平先生。
乐平先生画三毛名世。“三毛”在中国可以称得上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凡是读过《三毛流浪记》或看过同名电影的人,无不喜爱这个头上只有三根头发的流浪儿。
1947年初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张先生在回家的路上,在一个里弄口,发现有三个冻得瑟瑟发抖的流浪儿,单薄的衣衫挡不住凛冽的北风,身上披着几片破麻袋片,围着一个刚熄火不久的烤山芋的炉子,用嘴吹火取暖。乐平先生驻足默视很久,心里十分痛楚,当时他自己也实在无力帮助他们,只得黯然离去。当他第二天一早再经过那里弄口时,三个流浪儿已冻死了两个,另一个骨瘦如柴的也冻得只剩一丝微弱的气息了。一辆收尸车正要把尸体运走……
这幕场景,使一向热爱儿童的张乐平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对被抛弃在社会底层的这些流浪儿的不幸命运,他同情,也十分关切。他感到这世道太不公平了,决心用手中的笔,画出这些流浪儿的悲惨命运,向这个不合理的社会提出控诉。
就这样,乐平先生笔下的三毛诞生了。1947年6月15日,张先生的传世之作《三毛流浪记》开始在上海《大公报·现代儿童》上连载。一个鲜活真实的流浪儿,没有用一个文字,全用线条表现出来,他那心地善良、疾恶如仇、乐观自信、机智伶俐的性格被刻画得活灵活现。让每一位读者都感到可亲可爱。我就是在《大公报》上认识这位三毛的。
其实,早在1938年,我就与张乐平先生在金华见过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张先生在上海参加抗战,组织了抗日漫画宣传队,担任副队长。他于战争爆发的第二年带队到东南抗战前哨的金华从事抗日宣传,并举办画展。一天,我到金华八咏门外紫岩路一号《刀与笔》社另一位画家万湜思处玩,有幸见到了张乐平先生。这时《三毛流浪记》尚未面世,也不知道乐平先生就是“三毛之父”。那时,我只是个喜爱文艺的孩子,而乐平先生已是名满神州的青年漫画家了。他是我非常崇拜的偶像,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印象。而我在他眼中只不过是个十三四岁不谙世事的小孩,想来不会留下任何记忆。当我在庐山会议期间再次见到他,谈及这段往事时,他感到有点惊讶。他谈了在金华那段岁月中的一些人和事,万湜思(姚思铨)、金逢孙、《刀和笔》、《浙江潮》、八咏楼、紫岩路……有关金华的这一切,深深地留在他的记忆里。
在少儿读物“庐山会议”即将结束的前夜,我又到上海代表团下榻的招待所看望上海儿童文学办的朋友,正好碰上张乐平先生正在为向他求画的朋友画三毛。
当时围在他身后看他作画的人不少,许多新老朋友向他求画,都希望能得到一幅三毛。我是在乐平先生画的三毛教育影响下成长的,当然也急切地希望能得到一幅,看到他一连画了四五幅,先后被与他有深交的文艺界朋友喜滋滋地领去了,我才鼓起勇气说:
“张先生,请给我也画一幅,可以吗?”
“当然可以,不过,今天我实在太累了,等我回上海画好再寄给你,好吗?”
我随手递过去一张名片,请他按名片上的地址寄给我。说实在的,当时我也并不抱希望,心想他虽满口答应,也许是一种碍于情面的托词,只不过为了不想让我太失望罢了。他回上海后,人事纷纭,有忙不完的事,不可能再起意为我作画,我的愿望只能一直埋藏在心底。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回家后一直没有收到他的画,这件事就慢慢地在记忆中淡忘。
到了1980年初春的一天,我突然收到一封寄自上海华东医院的挂号信。拿在手上虽作了种种猜想,但想不出谁会在医院里给我写信。拆开一看,竟是一幅三毛,如获至宝,我感到分外的惊喜,眼眶里不由自主地掉下泪来。张先生卧病在华东医院的病床上,仍对自己的允诺牢记于心。这时,我才深深感到“一诺千金”这个成语的分量。在生活中,我们常见到形形色色“当面答应你,转身就忘记”的人,往往见怪不怪。当我收到乐平先生这幅“三毛”后,激动得彻夜没有睡着。谚云“烈火中炼金,诺言上看人”,乐平先生把自己许下的诺言看得比千金还重。看到这幅“三毛”,我仿佛看到乐平先生那颗金光闪烁的心。
——摘自2009年8月4日《金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