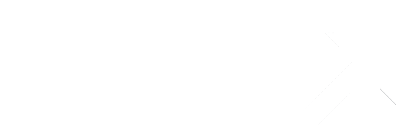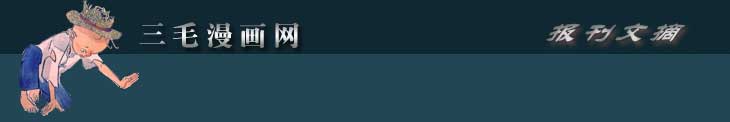
1949年的中国电影
从“三毛”开始
徐 江




共和国的历史伴随着一代人的记忆。这份记忆对于每个人都是精彩的,温暖的,值得用时间去慢慢梳理的。在我们的艺术版面中,我们更愿意用影像与音乐的方式去梳理这份记忆。通过记忆的通道,我们走进了自己的童年,走进了父辈的童年,也走进了共和国的童年。那些回响在耳畔的歌曲,那些电影院里的故事,那些发生在我们这片土地上的激情与浪漫、理想与追求,在我们的回忆中,向我们慢慢走来。
因为兼跨旧时代的终结和新时代的开启,1949年的中国电影是繁复而意味深长的。
唯一一次众星捧月
一方面,早期中国电影的写实传统,以及作为其变体的——“批判现实主义”美学风格仍有所延续,在这一年出现了不输于以往经典的《丽人行》(陈鲤庭执导,田汉、陈鲤庭编剧)、《乌鸦与麻雀》(郑君里执导,陈白尘等编剧)等重量级写实名片;另一方面,新的“人民电影”美学,伴随着共和国电影机制的逐步完善,已开始有条不紊地确立,上影、北影、东北电影制片厂(即后来的“长影”)三大国营制片基地正式建立并投入运转,第一部以获得解放的工人阶级为主人公的故事片《桥》,也由东影在1949年的5月推出……
传统电影美学的余音袅袅和新时代电影美学的初试啼声,可以说几乎是在同步的状态下进行的。参与摄制这两类电影的人——来自国统区的左翼资深电影天才,来自解放区的红色电影工作者,也将在日后的工作中通过不断融合交汇,构成整个“十七年”电影创作的重要支撑。不过,作为这一年最能代言中国新旧历史时段更迭、预示新老两种电影美学中和的影片,却不是上述影片,而是一部比它们更加具备了跨越时空能力的儿童片——《三毛流浪记》。
《三毛流浪记》改编自漫画家张乐平脍炙人口的同名漫画集。通过讲述流浪儿三毛在上海街头、贼窝、富家等社会不同层面的遭遇,控诉了一个行将末路的社会的罪恶与腐朽。片尾三毛和他的伙伴们迎来了解放,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天地。这个结尾后来有学者说不好,认为虽然配合了全国解放的新形势,却削弱了批判旧社会的力度。但批评者忽略了这部电影的主体观众是儿童,一个悲情式的结局,是不可能受到孩子和家长们欢迎的。从这个角度讲,《三毛流浪记》片尾流浪儿三毛的笑脸背后,偏偏又有着后来所有意在升华、拔高的影片所不及的意蕴。它身上兼具了老写实电影那种对原生态生活的描摹、提炼和新时代文艺所鼓励的希望。
电影的摄制班底也颇具1949年间电影圈新旧交融的特色:导演赵明(后来执导了《铁道游击队》、《年轻的一代》、《龙年警官》),严恭(作品有《祖国的花朵》,主题曲那首著名的《让我们荡起双桨》)是两个初次担纲的新人创作,编剧则先后由大名鼎鼎的阳翰笙、陈白尘和李天济(后两位没有参与署名,李天济是《小城之春》的编剧,日后还写过著名喜剧《今天我休息》)。电影作曲是著名的王云阶(日后还写了《六号门》、《林则徐》、《傲蕾·一兰》等片的音乐),主演“三毛”的是王云阶八岁的儿子王龙基,赵丹、黄宗英、朱琳等几十个一线大腕儿出来客串了一堆连登海报资格都没有的龙套角色,以至于被后人们称作是“中国电影史上唯一一次众星捧月”。
堪称经典记忆
《三毛流浪记》大约是在1929年美国的《人猿泰山》之后,世界上较早的几部直接改编自漫画书的剧情电影。而且与其他由漫画改编的电影不同,本片是在同名漫画集问世不久,就以近乎同步的速度开始拍摄的,也是主人公与漫画原著神形最为近似的电影之一。这都与主创人员,首先是与两位初出茅庐的导演,在当时条件下的热忱与探索分不开的。
《三毛流浪记》也是迄今为止,新中国所拍摄的黑白片与儿童片中,最具时空穿透能力的作品。1981年,它以32岁的“高龄”参加了戛纳影展的展映,并随后在巴黎的六家影院连续上映了两个月。这种业绩,即便在今天的亿元大导们看来,恐怕也是值得羡慕的。不过,那些亿元大导们这辈子怕很难再现《三毛》当年的这份荣耀了。一来时代在变;二来《三毛》中那种质朴的表演方式,那种浸透了创作者良知的苦中作乐和对生活的崭新希冀,都不是后人所能简单克隆的。它们永远都属于那特定的历史,以及坐标式的——1949年。——摘自2009年7月8日《每日新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