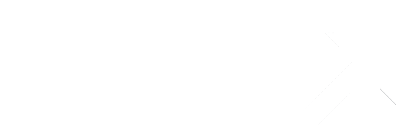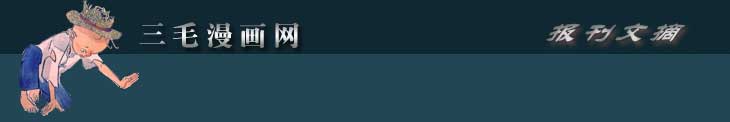
从流浪儿到新中国的好儿童
——三毛形象的转型
顾 铮
三毛也许是20世纪中国漫画史上最具大众影响的漫画形象。历经抗日战争前后两个时期、跨越1949年前后两个不同社会制度而生存下来,实为难得。就一个漫画人物形象跨越时代的长度来说,三毛的寿命也许是最长的一个,但三毛这个形象同时也是经历曲折最多的一个,从中可以细察到历史与政治话语变迁的征候。
从1935年开始,漫画家张乐平创造出一个名为三毛的可怜男孩,通过这个流浪儿的眼睛与生活遭遇,他展示当时社会世相,揭发人性中的黑暗之处。八年抗战结束后,他于1946年重拾三毛漫画,创作了《三毛从军记》与《三毛外传》。他的讽刺与批判的火力渐旺,并在内战时期的《三毛流浪记》中达到高峰。这些作品都因其讽刺与温情相揉的人性视点以及严正的现实批判态度而在当时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三毛流浪记》,连载时间长度恰与解放战争时期相合,对于助推革命胜利,影响人心向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现实意义不可小觑。
1949年之前的三毛成为一面透镜,人们从他的各种遭遇了解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社会矛盾,同时也一并接受了漫画作者对于社会现实的严肃批判。当然,人们同时也通过画家描绘的三毛的一系列遭遇,接受基于传统伦理观与西方现代普世价值观所给出的儿童定义。
然而,1948年10月29日的《大公报》上,张观保在《谈冰兄漫画》一文中,借谈廖冰兄的漫画,对于张乐平的三毛漫画作出了相当严厉的批评。此文称廖冰兄为“脚踏实地的人民漫画家”,认为廖冰兄的漫画“与‘人道主义’和‘温情主义’的《三毛流浪记》的作者张乐平有着明显的分别,他‘敢’直面惨淡的人生,而张乐平(的漫画)却是一篇虔诚的劝世文或醒世恒言”。显然,这篇文章的潜台词是,劝世文或醒世恒言是不够的,漫画家必须是战斗的。按照这篇文章的语气推测,温情脉脉的“温情主义”,几乎就要成为虚伪的同义词了。在这里,张乐平已经隐然成为廖冰兄的对立面,而“人道主义”也已经受到公然的蔑视,成为一个受到讥讽的名词。这个颇具政治性的评价,已经隐含解放后国家权力与意识形态对于漫画家以及一切文艺工作者的政治要求,并预示了漫画与三毛的命运。
因此,解放后有一年时间,张乐平迟迟不能或者说不敢举笔让三毛重新出现。1950年5月23日(值得一提的是,此日期是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日。),当时的上海市政府文化部门,“督促”上海漫画工作者联谊会为张乐平召开了一个“三毛创作座谈会”。经过讨论,与会者得出“比较一致的意见”,那就是“三毛作为已经深入广大读者心灵的艺术形象,不应改变其形象特征,年龄也应保持在原先的十岁左右的样子,让他生活在新中国的环境里,作为新中国的典型儿童形象来塑造,藉以反映新中国儿童丰富多彩的幸福生活”。为一个具有广泛影响的艺术形象与漫画家的创作,行政机构以群策群力的手法苦心诱导,使之纳入轨道,实为罕见。同时由此可知新政权对于运用一个旧时代的儿童形象在新社会展开政治宣传的苦心与吸纳有影响的画家的娴熟的组织工作手法。
1951年1月1日,三毛终于在解放后第一次出现在大众媒介中。在《三毛流浪记》中,三毛只是一个群众街头运动的旁观者,而这一次,三毛变为一个抗美援朝政治宣传中的主动参与者。在《三毛的控诉》中,三毛站在讲坛上,慷慨激昂,控诉抗战胜利后美军在中国的罪行,所有的人都望着他,他成为人们的视线焦点。以往不受人关注的“小瘪三”三毛成为了政治活动的一个焦点所在,而且以后还会多次以这样的方式出现在类似的场面。三毛在新社会的角色转变到了政治宣传的主体这个位置上了。
然而,作为已经并还要在政治宣传中担负重要角色使命的主体,三毛的过往经历在新社会看来却有些问题。1949年之前影响最大的三毛,当数《三毛从军记》与《三毛流浪记》。据说张乐平本人更喜欢的是《三毛从军记》。理由也许不难理解,那就是在军队这样的制度森严的国家机器中,小三毛以他的“出格”行为展现了他的机智、可爱、爱国心、朴实以及面对生死关头时的胆怯与市民气的狡狯。我们很熟悉的好兵帅克,其实也是在军队里大出其彩。发生在作为国家机器的军队与一个不受纪律约束的流浪儿之间的制度与人性的冲突,正是使人物出彩的最好设计。然而,正是三毛的这个“黑色”经历,在解放后显然成为了不光彩的经历。三毛如果想要生存并发展下去,其经历必须有所修正与改变。
这样的修正是逐步实施的。首先,在《三毛的控诉》(1951)、《三毛翻身记》(1951)等多部作品中,三毛作为一个新社会的成员,从积极参与政治生活与赞美现实开始树立自己的新形象。然而,正如《三毛翻身记》所提示的,经历复杂因此可疑的三毛在新社会不能受到充分的信任。在《三毛翻身记》中,三毛必须向组织解释清楚他是如何认识坏人麻皮阿金后才能进入工厂,成为工人一员。这反过来证明,修正三毛的经历就更有必要了。
1962年,张乐平创作了名为《三毛迎解放》的长篇漫画。他在陈述创作动机时说:“解放以后,三毛‘失踪’了一个时期。在此期间,不少关心他的读者,纷纷来信查访他的下落,希望他在受尽旧社会的欺凌压迫以后,也能够在新社会的阳光雨露中健康地成长起来。于是我又画了《三毛日记》、《三毛今昔》。在这些画幅里,三毛在各方面的关怀下,生活过得很甜,思想进步很快,脸上笑口常开,身上整整齐齐,完全是一幅新中国儿童的新面貌了。但是,这个三毛同《三毛流浪记》里的三毛之间,总好像缺少一点有机的联系,总使人感到他在解放以后的转变,来得比较突然。”
的确,从一个个性突出,但也不乏小市民气的流浪儿,转变成一个处处为他人着想,政治觉悟颇高的“新中国好儿童”,的确没有“有机”的联系,令许多读者觉得变化太过突然,无法适应。对于大多数仍然对于旧三毛记忆犹新的读者来说,新社会的三毛并不可爱,行为处事过于进步,既不冒失,也无急智。这样的形象与过去相比反差太大而显得突兀。为了让人接受他的进步转变,也便于他以后的表现可以比较自然地展开,用一个革命经历作为过渡也许会有效一些。但是,无论如何,这同时也意味着作者对于旧三毛的主动否定。
于是,我们看到了在以反抗与斗争为主线的《三毛迎解放》。流浪儿三毛在这部作品中终于变为一个积极地投入到国统区反蒋运动中的小英雄。他不止一次地与国民党军警特务发生正面冲突,斗智斗勇,并最后总以获胜告终。创作于1951年的《三毛的控诉》与《三毛翻身记》中的三毛还只是一个觉悟低的流浪儿,而在《三毛迎解放》中,三毛先是自发地参加“反饥饿、反迫害”的示威游行,并在游行中攻击警察,继而将证券交易所的名字改为“卖人交易所”而遭捕,终因监狱人满为患而被开释。在他卖报时,遭遇以《少年报》为掩护的地下党,并成为小通讯员,投稿控诉时弊,又到贫民窟发动群众,接受地下党的任务发传单贴标语,侦察国民党兵营,发现特务监视少年报社时紧急报信,使报社地下党成员脱险,直到迎来上海解放。
重新编写了三毛历史之后,他就要作为一个“新社会的好儿童”,在国家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发挥“先锋模范”带头作用了,除了通过助人为乐这样的“好人好事”为儿童树立榜样,充当政治社会化的标本之外,已经别无作为。其实,让三毛继续生存下去勉为其难。如果三毛是“新社会的好儿童”,那么他身上就不应该有可以讽刺的地方。如果他仍然有可以讽刺,即使是善意的讽刺的地方,那也只能证明他不是一个社会主义“新人”。现在唯一可以做做文章的地方是以三毛的新生活来证明两个社会的天壤之别。如果说当初从一个儿童的苦难遭遇着手,来证明一个旧政权的合理丧失是成功的,而且也有着足够的说服力的话,那么,在今天,则是从新中国儿童的幸福生活着手,来证明一个政权的合法性。当然,这样的创作,还必须把传统话语对于儿童的伦理与道德诉求以及国家政治话语的要求糅合起来。这些要求的内容是集体主义、服从、忠诚、毫无私心等。
社会政治化的过程不仅让他成为一个模范,更重要的是通过他的行为以及由此获得的肯定,来影响与暗示其他儿童甚至成年人。
国庆十周年,张乐平发表了《三毛今昔》。他选取旧作《三毛流浪记》中的一些画面作为旧时代的苦难,另外新画三毛在新时代的幸福生活,以其新旧对比宣传新气象。将两个画面并置,使其产生某种意义的手法,一直是艺术表现中的常用形式。在《三毛今昔》中,“忆苦”与“思甜”本身就构成了直观的宣传效果,反差极强地并置时空。在《三毛流浪记》中,“想去上海”中的三毛不仅不能搭上国民党长官样子的人的汽车,还挨了车主的耳光,并被溅了一身水。而在“春游遇雨”中,“遇雨”的三毛被干部接上自己的汽车,证明了新社会的新风与干部亲民。不仅如此,三毛也开始被以各种方式组织进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去。在《三毛今昔》中,三毛成为了捡废品支援国家建设的活动的带头者,他也在同辈群体中指挥高唱《东方红》。
当然,在《三毛今昔》之前,三毛就已经积极地投身于许多政治性活动与运动。比如,在1950年到1965年的《三毛日记》中,就有“快来签名,保卫和平”、“爱国的三毛”、“国庆大游行”等这样的明显具有时事政治和国家大事的正面题材。在这些作品中,三毛成为了国家宣传动员的先锋。一个最极端的例子是,在“三毛的梦”中,通过否定一个儿童的求学梦想来宣传务农光荣的口号。而“是他弄坏的”则展现了一个敢于揭发损害公物者的三毛。儿童善于模仿的特点,也被用于规劝孩子向成人干部、模范学习。于是,在《三毛日记》中就有了“我们也来开会”、“鲜花送模范”等作品。在“我们也来开会”中,开会这种成人的政治活动取代了符合儿童特点的游戏。
三毛获得广泛同情的孤儿形象,强化了对旧社会的批判,这当然是非常有效的攻击。但在新社会,他仍然是一个没有家庭幸福的孤儿。有学者发现,许多关注中国革命的外国人,往往只能在像托儿所、幼儿园、学校这样的社会机构与组织中看到中国儿童,“透过种种信息,一些外国学者对中国孩子的状况提出了质疑。他们注意到,随着‘妇女投身社会’的制度化和家族主义价值取向的被否定,在中国的家庭/孩子关系和国家/孩子关系中发生了某种变化:孩子不再只属于家庭、家族,而更属于国家、社会。‘孩子’作为‘祖国的未来’、‘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他们的哺育、教育、出路安排等等不再只是父母的义务和权力,在相当程度上被认为是国家、社会的事”。证之于“文革”之前的作为“祖国的花朵”的三毛漫画中的各种活动,事实的确如此。跨越家庭这个环节直接与祖国这个概念联系起来,更有利于强化国家话语。或者说,没有家庭更有利于突出国家对于个体直接发生的社会政治作用,国家直接担负起儿童的价值观与人格形成的任务。因此,被要求塑造为新中国儿童典型的三毛虽然是一个孤儿,却可以是一个幸福的孤儿。
我们必须体谅张乐平在意识形态泛化的大势下,为使三毛这个因批判现实而不朽的形象在新制度下的存续所作的努力。即使在阶级斗争之弦越绷越紧的时候,张乐平仍然没有让三毛以对待敌人的方式去对待他的周围人。这可以看出他的底线所在。三毛只是在做一个符合意识形态要求的好孩子。从某种意义上说,三毛这个符号化的形象,其生命力在于其形象的符号化而行为的不符号化,如此才可有其出格的个性,才能被人寄托理想与希望。然而,一旦他的形象既已符号化,而且行为也因政治社会化而符号化、成人化,其结果只能招人疏远甚至倦怠。从这一点看,三毛仍然有不少值得议论的话题。
——摘自《童话童画》,2009年4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