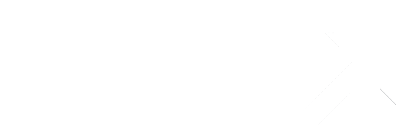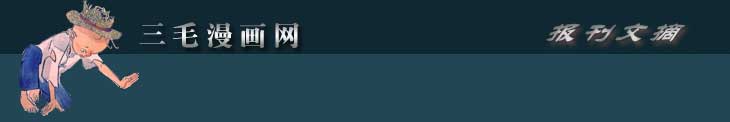
想起了三毛
耿 法
记得上小学时就对张乐平的漫画《三毛流浪记》爱不释手,那个头上卷曲着三根毛的可爱又可怜的三毛形象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几十年过去了,至今不曾淡忘,可见其影响之大。《三毛流浪记》使我知道了旧社会流浪儿童的悲惨生活和不幸遭遇,也学到了三毛身上的善良、同情、勤劳和不怕吃苦的优点,长了不少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茅盾先生早年也写过一篇描写旧上海流浪儿童生活的小说《大鼻子的故事》,我那时也看得津津有味,但毕竟不如张乐平的三毛那样生动、直观而形象,对少年儿童的影响那么强烈,记忆那么清晰。
可是解放后,张乐平具有强大艺术生命力的“三毛”创作竟然中断了。“三毛”创作为何中断?近读文汇笔会编辑部编的“笔会60年珍藏版”《一个甲子的风雨人情》(文汇出版社2006年8月第1版),书中收录了张乐平先生发表在1957年5月18日文汇报上的《三毛何辜》一文,说得十分清楚。解放前,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曾指责张乐平用三毛形象揭露当时社会丑恶面貌“表现太残酷了,太冷落了”,画家毫不畏惧,因为广大读者支持张乐平画三毛,这是支持真理和正义,画家为此受到鼓舞。解放后,读者十分关心三毛,要求画家重画解放后的三毛。张乐平写道:“就在这个时期,我听到了不少关于三毛的议论。这些议论大大地影响了我的创作情绪。有人说:‘三毛是流浪儿,就是流氓无产阶级,不值得再画’;另外有人说:‘三毛太瘦了,他的形象只适合于表现旧社会的儿童,而且他只有三根毛,显得营养不足,即使值得再画,也应该让他头发长多起来,胖起来,这才是新面目。’……”更有甚者,1952年文艺整风时,有人做鉴定似的说,《三毛流浪记》等于《武训传》。这样上纲上线问题就更大了,弄得画家担惊害怕,好几天睡不着觉。后来虽然得到夏衍同志的支持,又得到报社的鼓励,张乐平鼓起勇气画了《三毛翻身记》,但由于“无法摆脱上述的一系列的清规戒律的影响,在思想上缩手缩脚,它在风格上与‘流浪记’相比真是大不相同。”当时报社既给了画家鼓励,又给了题材上的种种约束,譬如要画家结合每一个政治运动来画,如土地改革,反对美帝武装日本,镇压反革命等等,“结果弄得三毛很神秘,当然没有画好。”此时的三毛只有外形而无灵魂,失去了特有的艺术形象和魅力,于是,三毛死了!张乐平先生只得发出“三毛何辜“的质问与呼吁。这篇文章发表在反右运动前夕,说出了埋藏在画家心底的真话。后来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直到史无前例的“文革”发生,无辜的三毛自然更无出头之日了。
现在看起来关于三毛创作的遭遇似乎很可笑,但别笑得太早,种种教条主义清规戒律的束缚是否已经彻底消除了?作家、艺术家是否敢于直面生活,保持一片强烈而纯真的爱心,真实而深刻地反映当代流浪儿童的现状呢?如今我国的社会正处于转型期,由于各种原因,造成流浪儿童大量增加,已成为明显的社会问题之一。别有用心的坏人背后操纵流浪儿童、残疾儿童在城市里乞讨、偷窃、行骗的事件也时有所闻。然而又有几位作家、艺术家像当年张乐平一样以流浪儿为题材,扎扎实实地深入生活,正视现实,精心创作出新的三毛形象,引起全社会对流浪儿童的重视、关心、帮助和疗救呢?儿童世界并不都是伊甸园,英国作家狄更斯当年有《雾都孤儿》,中国作家黄谷柳也曾著有《虾球传》,而笔者至今尚未看到新时期我国作家的这类力作;前苏联有马卡连柯的《教育诗》,真实描写如何赋予一群流浪儿童新生的故事,但我们这儿除了多年前有一部电视剧《寻找失去的世界》外,几乎没有其他此类作品,更不要说漫画一类创作了。这里既有观念问题,也有缺乏生活问题。张乐平先生在文章中说:“漫画的性质与其他画种是不同的,在吸取题材上和创作方法上都有它的特殊性。画家需要接触更广更多更深刻的生活。记得我在创作《三毛流浪记》时,经常深入到旧社会各个角落里去,甚至特地换了破衣服深入到流浪儿童中去。有时画不出,就到街头上去兜,效果很好。”如果没有这种精神和作风,是不可能诞生《三毛流浪记》这部杰作的。当然不止是漫画创作,其他形式的文学、艺术创作也必须深入生活,才能出好成果。试问今天的儿童文学作家和艺术家,能否继承和发扬老一辈的传统呢?
多么希望儿童文学界和艺术界多出几员猛将,多么希望有新时期的三毛形象和生动故事的优秀作品问世!——摘自2006年10月31日 大河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