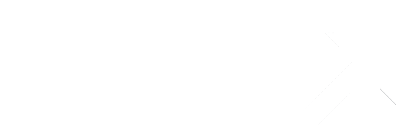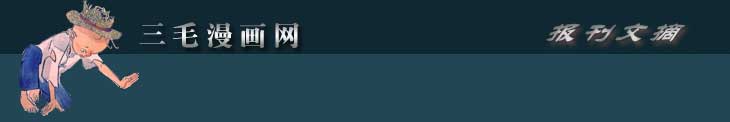
听宋庆龄说“对不起”
虞子骏
1949年初,中国福利基金会为了救济上海的贫困儿童,特请漫画家张乐平画三毛,准备在“三毛乐园”义卖,但不久,张乐平突然病了,而“乐园”开展在即,我的一位在会同学把我从学校拉去救急。那是3月的一天,我应约来到霞飞路虹桥疗养院前(今徐汇区中心医院)的一座大草房里,一位工友将我引到一间较大的会议室说,大家要开会,请我在这里稍等。我独自站着,打量着这个陌生的地方,就在这时,突然有位中年女士轻轻地走了进来,见我在就用带浦东口音的上海话对我说:“对不起,我来搭把椅子”。就又匆匆出去了。呀,这不是孙夫人吗?以前我在照片里看见过,可现在真的见到她了,而且还和我说了话。这就是我见到宋庆龄的第一面,这第一面虽然只有短短几秒钟,但这印象却永远铭刻在我的脑海中,并影响了我的一生。在基金会,她是主席,是孙中山先生的夫人,被人称为“国母”,而现在,我只是一个外人,一个学生,站在会议室中,她非但不问“你是谁?来干吗?”反而认为自己突然闯了进来,打扰了我而感到抱歉,并告诉我“我只是来搭把椅子的”。因为临时开会,集中在办公室,椅子不够,她怕别人站着,特地自己来搭把椅子,从这件小事使我看到了宋庆龄的为人、她的修养、品格和对同事的爱,实在让我钦佩,久久不能忘怀,这也是使我最终来到少年宫的重要缘由之一。
宋庆龄“把最好的东西给予儿童”的精神一直指导着我的工作,她说:“把最好的东西给予儿童”应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物质的,一个是精神的,她已把上海最漂亮的“大理石大厦”给了孩子,接着希望少年宫能用最好的老师来培养出一批批最好的人才,本着她“严师出高徒”这一信念,我千方百计地为美术各组请来了最好的老师。在绘画组,虽已有了我这个专任教师,不可能再请兼职,但我以“见面会”、“座谈会”、“访问”等形式让孩子接受名家的教育,我多次请张乐平讲述创作“三毛”的动机和经过,请万籁呜讲演动画片、木偶片和剪纸片的制作;请乐小英介绍画漫画,又带组员去访问我的老师雕塑家张充仁先生,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而举办的“被盗国家珍贵文物展”中请国画家、收藏家唐云编写部分说明;国画组,我请来了著名花鸟画家江寒汀、乔木作兼任指导;为书法组, 我找到化工研究所和光学仪器厂,把周慧珺和张森请了出来(他们后来成为上海书法家协会第一任和第二任主席),以后又从中国画院请来了钱茂生;大家知道,面人组的指导是赵润明,有名的“面人赵”,但他的来历却很少有人了解,开宫不久后的有一天有人对我说:少年宫门外有个人在捏面人,做得很不错,很好玩,我就出去看了,一个40多岁的艺人正埋头做着,技术熟练,步序清楚,特别是形象相当逼真生动,和一般街头艺人不一样,于是我决心把他请进来做了面人小组的指导,后来工艺美术研究所成立,他成了工艺美术师,面人专家。接着我又请来了剪纸名家王子淦,并增开了剪纸小组。严师出高徒,我们少年宫美术各组的确为国家培养了不少优秀后继人才。
1950年,中国福利会根据周恩来总理和宋庆龄的决策,把办会方针确定为“实验性、示范性、加强科学研究”,为下属各单位指明了工作方向。在解放初期,少年宫是个新生事物,它从苏联来,但又不能全和苏联一样,怎么搞,大家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我们美术组虽然已经开了些有民族特色的国画、书法、刺绣、剪纸、面人各组,但在绘画方面仍脱不了一套苏联模式,大部分活动都是在室内写生、画石膏像。欣赏苏联和俄罗斯画家作品,也画些儿童生活的创作,但形势在发展,60年代,绘画组开始将孩子引出室门,投身到社会中去。我们在七宝、松江九亭和上钢三厂设点,经常让孩子去体验工农生活,当场画速写,回来后又将先进人物和事迹绘成连环画再去宣传和展览,使组员在思想和技术上得到充分的锻炼,效果很好,这些组员后来都成了连环画创作能手。
——摘自《我与中国福利会少年宫》,2003年9月中国福利会少年宫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