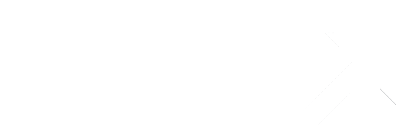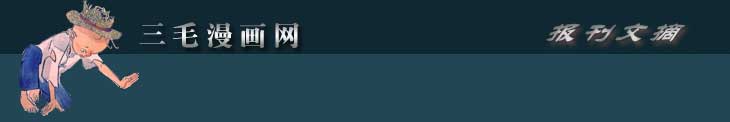
我少年、青年、中年、暮年心中的张乐平
黄永玉
乐平兄大我十四岁,我大三毛十一岁,有案可查的一九三五年《独立漫画》上伟大的三毛出现的时候,乐平兄二十五岁,我呢?十一岁。我没见过这幅“开山祖”的三毛。唉!三毛活到今天毕竟是六十多岁的人了。
读三毛,是在《上海漫画》和《时代漫画》上。
事实如此,我的“美术事业”是从漫画开始的。
那时候家乡的风气颇为开明进步;新思想、新文化、新文明不断鼓动年轻老师们的进取心,一波一浪地前赴后继。他们从上海、北京订来许多进步的杂志报章相互传阅,我们这些小学高年级学生由此受益之处,那就不用提了。我们抱着《上海漫画》和《时代漫画》不放,觉得它既是让我们认识世界的恩物,又是我们有可能掌握的批判世界的武器。
我们家乡是块割据的土地,统治者掌握湘西十来个县权利,谁来打谁!国民党、蒋介石那时奈何不得。所以有一二十年的偏安局面。
我们模仿着《上海漫画》和《时代漫画》的风格在壁报上画点讽刺当地流俗的作品,甚至老着脸皮贴到大街上去,却是因为心手两拙,闹不出什么有趣热烈的反响。
不过,这个小群落的自我得意倒是巩固了一种终生从事艺术的勇气和毫不含糊的嘲讽眼光。
一九三六年四月四日儿童节,父亲给我的礼物是一本张光宇、张正宇兄弟合著的《漫画小事典》。
这包罗万象的万宝全书教会我如何动手和如何构想,把身边的人物和事情变成漫画。我一边欣赏,一边模仿,找到了表达力量。学着把身边的事物纳入《漫画小事典》的模式里来。仿佛真感觉到是自己创作的东西。
我知道世界上有伟大的张光宇、张正宇、叶浅予、张乐平……一口气能背出二三十个这样的“伟人”,奔走相告,某一本新漫画杂志上某一人又画了张多么精彩的漫画,于是哥儿们一致赞赏:
“这他妈狗杂种真神人也!”
“王先生”、“小陈”,开阔了我们对上海社会生活的眼界,“王先生”的老婆很像南门外丝烟铺费老板的老婆刘玉洗。越看越像。简直笑死人!
“王先生”和“小陈”骂人“妈特皮”,我们也一起认真研究过,究竟跟本地用的“妈个卖麻皮”是不是一样东西。
上海人居然也骂粗话!了不起!
我们没过过他们的日子,我们没有“王先生”和“小陈”那么忙,那么热闹。我们成天看到的是山,是树,是河,他们呢?是洋房子。“看高房子不小心会掉帽子”,嘿!说这话的城里人真蠢!你不会按着帽子才看吗?
“三毛”不同。“三毛”完全跟我们一样。人欺侮人,穷、热、冷、累、打架,他成天卷在里头混,我们也成天卷在里头混。他头发虽然少了点,关系不大的。他比我们长得好!他可爱!像我们,满脑壳头发有卵用!
你别瞧“三毛”三笔两笔,临摹容易,自己画起来特别难;不信你试试看!这不是学的,是修炼出来的。
左边、右边、正面、侧面、上边、下边,怎么看都是他。又没有这么一个真人让写写生,完全靠自己凝神定位。
我们既然晓得世界上有个张乐平和许许多多同样是人的人,又晓得人和人虽然都要吃饭、吃猪脚和炖牛肉、喝汤,更晓得人和人是多么不一样。
有一天,我跟同班吉龙生的爹、正街上蒸碗儿糕的吉师傅,论到这个问题。
“你晓不晓得张乐平画的三毛?”
“卵三毛!”他说。
“你晓不晓得三毛是一个人凭空画出来的人物?”
“晓得有卵用?又不当饭!”
“猪也吃饭,狗也吃饭……”
“兔崽子!你不滚,老子擂你!”他追出来。
我觉得他这种人是无可救药了,决定不救他。
自从我每天画漫画以来就觉得自己开始高级。先是画周围人的样子。我父亲有个大胖子好朋友叫做方季安,一脸烂麻子,虽然是军法官,却是个非常和气的伯伯。
我在马粪纸上画了他的全身像,然后周身剪下来,让三岁的弟弟拿去堂屋让他们看。
爸爸首先大笑,叔叔伯伯们也大笑,送到方麻子伯伯面前。方伯伯也咧嘴大笑,一边笑一边骂:
“准是‘大蠢棒’(这当然指的是我,我排行第一)画的!叫他来,看老子军法从事!”
爸爸事后翻着《时代漫画》时顺口告诉我:
“你画方伯伯像是像,神气不够。你看看人家张乐平的三毛和周围的那些人,一个是一个的动作,神气,表情,各有各的样子。不能只是像。”
像已经不容易,还要动作,还要神气,爸爸呀,爸爸!你以为我是谁?
我有时没有纸;这里的纸只是毛边纸、黄草纸和糊窗子的小北纸,临摹带色的漫画是用不得的,起码要一种印《申报》的报纸。这种纸,纸店不常来;来了,我碰巧把钱吃了东西,只好对着铺子干瞪眼。要知道,做人家儿子时期,经济上总是不太松动的。到第二天省下零用钱赶去买纸,纸却卖光了。
《时代漫画》和《上海漫画》里头还登有好些外国画家画的画,墨西哥、法国、德国、英国、美国……我不懂。我不敢说它不好。奇奇怪怪的眼睛和脑袋,乱长的嘴巴,说老实话我有点怕,像推开一线门缝似的,我往往只掀开半页纸偷偷地瞟它两眼,很快地翻过去。我明白这是长大以后的画家看的东西,是有另外的道理的。
有一天,我忽然在《良友画报》上看到三四个人在海滩上赛跑的照片。打赤膊,各穿一条短到不能再短的裤子,没命地跑着。题目是《海滨之旅》。小字印着左起叶浅予,张乐平,梁……梁得所……(梁得所是谁?干什么跟着跑?)
远是远,不过都能理清面目。这三个家伙长得都他妈的俊;叶浅予高大像匹马,还有撮翘翘胡子;张乐平的鼻子、额头上撮起的头发都神气之极,像只公鹿;梁得所腰上有根细细的白带子跟着飘,像个洋神仙。
他们都这么漂亮。他们不好好画漫画,到“海滨”来“之旅”干什么?
画漫画的都要长得这么漂亮那就难了!我长大以后肯定办不到!我也不好意思穿这么窄的短裤让人照相,万一“鸡公”露出来怎么得了?
这倒要认真考虑考虑了,长大后到底画不画漫画?
不过,画“王先生”、“小陈”的叶浅予是这么副相,张乐平是那么副相,我可见到了。我会对街上的孩子和同学说:
“考一考你们!叶浅予、张乐平长得是什么样?”
我又说:
“……不知道吧!我知道!他们长得比你们所有的这帮死卵都漂亮!”
抗战了,打仗了,我在福建南方。学校搬到山里头。
学校图书馆不断有新书、报纸、杂志、画报寄来。
《西风》、《刀与笔》、《耕耘》、《宇宙风》、《良友》、《人世间》、《抗战木刻》、《大众木刻》……记不住、说不完的那么多。
既然是抗战了,所以每时每刻都群情激昂,人声鼎沸。
接着图书馆里又涌来上海、武汉、香港、广州各个地区宣传中心寄来的漫画、木刻艺术的印刷品。
我们心中仰慕的那一大批漫画家都仿佛站在炮火连天的前线。每一星期都看到他们活动的消息、新的创作。
学校一位美术老师朱成淦先生帮我们写信给浙江金华的野夫和金逢孙先生,各人交了八角钱,入了中国木刻协会。从那时起,我们的艺术世界扩大了,懂得自己已经成为艺术小兵的价值。
除了伟大的叶浅予、张乐平这一帮“家”之外,还有陈烟桥、李桦、野夫、罗清桢、新波另一帮大“家”。
“漫木”的概念,就是“漫画”与“木刻”的合称。
学校有壁报。我们自觉已经长大,能够自己画出漫画和刻出木刻来。逢有游行和集会,也懂得赶忙把那些出名的漫画和木刻作品放大画在布上用来布置会场,或作游行旌旗招牌。
这么一直忙碌、兴奋,为了抗战我们就这么慢慢活着,长大。
张乐平和其他漫画家不同。别的漫画家难得见到速写工夫,张乐平时不时露几手速写。准确,生动,要害部分——比如眼神,手,手和手指连接的“蹼”的变化,全身扭动时的节奏,像京戏演员那种全身心的呼应。我既能从他的作品得到欣赏艺术的快乐,又能按他作品的指引去进一步观察周围的生活。
每一幅作品都带来一个惊讶和欢欣。他的一幅“打草鞋”的速写,我从报上剪下来贴在本子上,翻着翻着,居然翻得模糊不清了(堪怜当年土纸印的报纸)。
他还画了一套以汉奸为主人翁的《王八别传》的连环画,简直妙透了、精彩透了!笔墨挥洒如刺刀钢枪冲刺,恨日本鬼,恨狗汉奸,恨得真狠!而日本鬼的残酷凶暴和狗汉奸的无耻下流也实在难找替身。
他想得那么精确传神,用笔舒畅灵活且总是一气呵成。看完这四幅又等待下四幅,焦急心情,如周末守侯星期天,茫然心情是十天半月后的等待。
这种等待,这种焦虑,这种迫切的遗痕,在我今天的国画写意人物刻画和笔墨上随处可见。我得益匪浅。如有遗憾,那只是我当时年幼无知领会不深。
在学校,我有个读高中的同学李尚大。这人与宰相李光第是同乡。他是学校有数几个淘气精的偶像。胖,力气大,脾气好,能打架,有钱,而且是个孝子。
暑假到了,同学回南洋的回南洋,回上海的回上海,回广东的回广东,回四面八方的回四面八方,剩下七八个有各种理由不能回家的人留在学校。那么空荡荡的一座文庙,一出去就是街,就是上千亩荔枝、龙眼树,就是蓝湛湛的一道河流,漫无边际的沙滩,太好玩了。
就缺个领导人。
当然是李尚大。可惜他也要回去。他家离城里百八十里。他常邀请一二十个高中同学步行回家。我们想去,不准!嫌小,半路上走不动怎么办?
他家是我们想像中的“麦加”,听说房子又好又大,住五六十人也不要紧。妈好,煮饭给大伙吃,从不给儿子开小灶,一住就是一两个月。像是大家的妈。
忽然听说他这个暑假不回家。
你想我们多高兴?他胖,怕痒,我们一拥而上挠他的痒,他要死要活地大叫,答应请我们吃这个那个。
我们是他的“兵”,他出淘气的主意,我们执行。他会讲出其不意的故事,一句一句非常中听。
听说他妈梅雨天气放晴之后,就会在大门口几亩地宽的石板广场上搬出一两百个大葫芦,解开葫芦腰间的带子,一剖两半爿,抖开全是大钞票。她晒这些发霉的钞票。
想想看,又有钱,又会打架,又喜欢跟我们初中生在一起,脾气又好,我们怎能不服?
晚上,大成殿前石台上一字排开,他教我们练拳脚、拉“先道”、举重……我想,他也自我得意,也喜欢我们,要不,干吗跟我们在一起?
有年开学不久,祸事来了。学校一个教员在外头看戏跟警察局长太太坐在一排出了点误会,挨打后鼻青脸肿逃回学校,让大同学们知道了。这还了得?打我们老师!出去将警察局巢穴踏了,局长、股长……齐齐整整、一个不漏地受到一两个月不能起床的“点化”。
事情闹大了。政府有政府的理,学校有学校的理。架,是帮学校打的;打警察及诸般人等又是违法行为。学校的后台硬,政府说到底也奈何不得,做了个“面子”行动,开除三个同学,一个是我坐后边课桌的同班同学,两个高中生,其中之一是李尚大。
学校这么做,人情讲不过去吧!开除这三个同学布告贴出,接着是为他们开了个欢送会。
李尚大走得静悄悄,几天后我们才知道。可以想象,多么令人惆怅!
就那么走了!一走五十年我们才再见面,这是后话,且按下不表。
李尚大走的第二年,我也打坏了人,头上流血,有三个伤口。这一场架一不为祖国,二不为学校,百分之百地为自己;学校姑念是“战区学生回不了家”,“两个大过、两个小过,留校查看”。
我原本就不喜欢读书,成天在图书馆混,留了无数次级已经天地一沙鸥似的落寞,再加上来这么个仅让我留一口气的处分,意思不大了,人已经十五六岁,走吧!就这么走了。
……这个李尚大在哪里呢?他不可能再念书了吧。方圆一千里地的著名中学他哪间没念过?那么,找到他岂不是没一线生机?他四方云游去了,找不到了。此念绝矣!
世界上还有谁呢?
张乐平!
认识张乐平吗?当然认识!那么多年,熟到这份程度,怎能说不认识?只可惜他不认识我。
报纸上说他在江西上饶漫画宣传队当副队长,叶浅予走后他当正队长。找到他,不让我当队员当个小兵也行。他没有什么好怕的嘛!我又不会抢他的队长位置。
江西上饶怎么走法?有多远?钱不钱倒是不在乎,我一路上可以给人画像、剪影,再不,讨饭也算不得问题吧?又没家乡人在周围。我如进了漫画宣传队,就像外国人爱唱的那两句:
“到了拿波里,可以死了!”
张乐平这人也怪,几年来,他一下这里,一下那里,先是南京,后是武汉,又是江西上饶三战区,一下金华,一下南平,一下梅县,一下赣州,也不知是真还是假。我如果下决心跟着追下去,非累死不可!于是老老实实在德化做了两年多的瓷器工人,在泉州和仙游做了两年多战地服务团团员,半年小学教员,半年中学教员,一年民众教育馆美术职员。这几年时间里,画画、刻木刻、读书、打猎、养狗、吹号、做诗,好像进了个莫名其妙的大学,人,似乎是真的长大了。懂了不少事,凭刻木刻画画的身份,结识许多终生朋友。
稍微稳定之后又想动,好朋友帮我设想一个方案:“军管区有团壮丁要送到湖南去,你不如跟他们一起去,虽然说步行三个省路程稍微远了点,你省钱啦!一路上有个伴啦!先回老家看看爹妈,歇歇脚,再想办法到重庆去,那近多了是不是?到重庆后有两个方案,一个是进徐悲鸿的美术学院,一个是设法到延安去,那地方最适合你,到时候我再帮你忙。我这里有三封信,江西赣州剧教队曾也鲁、徐洗繁一封,长沙一封,重庆一封,你要放好。事情是说不定的,若到半路上出意外,你就留在赣州剧教队。赣州是两头的中间,留下来也未尝不可,到时候再说吧!”
从永春县出发,凄风苦雨开始,一千里?二千里?三千、四千、五千难计算,就靠两只脚板不停地走。那时候,两眼务必残忍,惨绝人寰的事才吞得下去,才记得住。半路上,营长、连长开始在我背后念叨,指指点点。非人生活,壮丁急剧减员;看那些眼神和阵势,似乎是要热烈邀请我参加壮丁队的行列。此时不走更待何时?
教育部剧教二队在赣州城边的东溪寺。
为什么一个演剧队会驻扎在寺里头呢?因为它根本不像个寺;毫无寺的格局和章法。东一块、西一块,顺逆失度,起伏莫名,不知是哪位粗心和尚的蹩脚木匠朋友的急就章。正如北京人常说的一句话:“瞧哪儿哪儿都不顺眼。”没一间正经房子,没一个正经角落,楼梯不像楼梯,板墙没板墙样子,天井不像天井。绝望之至,霉得很。
幸好剧团的人都有意思,极耐看。
和我有渊源的是徐洗繁兄嫂;算得上老熟人的陈庭诗(耳氏)兄;谈得来的是殷振家兄、陆志庠兄。我在队里太小,无足轻重,是个见习队员。实在说,根本没有我做得了的事。留下我,是看那两封信的面子,小小善举而已。
耳氏打手势告诉我,张乐平也在赣州。
“啊!”我像挨电击一样。
他又打手势说:
“就住在附近伊斯兰小学里。”
“啊!”我又来了一下。
一天之后,耳氏带我到张乐平家。
从东溪寺出大门左拐,下小坡,走七八步平坡,再下小坡,半中腰右手一个小侧门,到了。
穿过黑、臭、霉三绝的“荒无人烟”的厨房,下三级台阶,左手木结构教室和教室之间有一道颇陡的密封长楼梯直上张公馆——一间小房。
第一次见到乐平兄嫂的心情,我已在慌乱中遗失了。好像我前辈子就认识他们;我心底暗暗地问他们:我找了你们好多年,你们知道不知道?他们两位的样子完全就是我想象中应该长的那个样子。在这个家中,我满脑、满胸的融洽。
周围是木板墙,小桌子,双人床,一张在教堂结婚的盛装照片(后来才说明那是用一张洋人照片改的),两张为中茶公司设计的广告,一个小窗。
后来我送了一副福建仙游画家李庚写的对联给他:
雨后有人耕绿野,月明无犬吠花村。
他挂在中茶公司广告边上。
几个月间我常常上他们家去。有两个跟我年纪差不多的朋友也常去串门,一个名叫高士骧,一个名字忘了。小高的笑貌至今仍是我们珍贵的想念。(小高你在哪里?)
那时候的老大哥、前辈,很少像今天这样有许多青年围绕帮忙。老一代的也很年轻,日子艰苦但身心快乐。年轻人对于贤达的尊敬很学术化,很单纯。对国难家仇和蒋介石的蔑视,大处看,是种毫不怀疑的凝聚力量。在群众生活的小处,即使曾经有过龃龉,上门骂娘,楼上楼下吵架,至今回忆,恩怨消融殆尽,只剩下温馨和甜蜜;连当年最遭人嫌弃的家伙,也仿佛长着天使的小翅膀在脑门前向你招手微笑。流光倏忽并非时人宽宏大量,而是上天原宥这些苦难众生。
乐平兄逝世很令我奇怪,其实活了八十几岁已经很不简单。我只是说,乐平兄怎么会变成八十几岁?就好像我有时也想自己怎么会一下子七十多岁一样。一切都活在永远的过去之中。
有人说,抗战时期,某某人如何如何受苦;有的人自己也说,如何如何受苦。他忘了,抗战时期,谁不受苦?幸福这东西才不公平;苦难却总是细微、公平地分摊在大家肩上。所以卡夫卡说:“要客观地看待自己的痛苦。”
乐平兄在人格上总是那么优雅。没叫过苦,没见过他狂笑失态,有时小得意时,大拇指也翘得恰到好处,说一句:“这物事邪气崭格!”
我这人野性得很,跟着他却是服服帖帖。那时,我没有什么值得他称赞的。不知怎么心血来潮,用泥巴帮殷振家兄做了个可以挂在墙上的漫画人像,还涂了颜色和微微发亮的鸡蛋清。乐平兄看了似乎是在为我得意,平举着我那作品,斜眼对振家兄说:
“侬哪能生得格副模样?勿是一天两天工夫格……”
再回过头对我说:
“哪!侬把我副尊容也做一个!好哇?”
我一两天就做好了,送去伊斯兰小学。他见了很开心:
“喝!喝!喝!”又是平举起来眯着眼睛看:
“侬哪能搞起这物事来格?侬眼睛邪气厉害,阿拉鼻子歪格浪一挨挨也把侬捉到哉!”
他真的在墙上钉了小钉子,像挂上了。
过了半个月或是一个月,耳氏打手势告诉我,乐平反手做一个特别的动作,碰断了漫画像的鼻子,再也补不起来,很懊恼,偷偷把它藏起来了。
记得他那时也画三毛。我不记得什么地方、什么报纸用的。他坐在窗子边小台子旁重复地画同样的画稿。一只手拐不自然重画一张,后脑部分不准确又画一张,画到第六次,他自己也生起气来。我说:
“其实张张都好,不须重画的。”
他认真了,手指一点一点对着我,轻声地说:
“侬勿可以那能讲!做事体要做透,做到自家呒不话讲!勿要等人家讲出来才改,记住啦杭!”
一次雏音大嫂也告诉我,他画画从来如此,难得一挥而就。
这些话,我一直用到现在。
乐平兄和我比起来是个富人,他在中国茶叶公司兼差。不过他一家是四个人,所以我比他自由。
他有时上班前到东溪寺找我,在街上摊子喝豆浆吃油条糯米饭。我有一点好处,不噜苏,不抢着说话;自觉身处静听的年龄,耳朵是大学嘛!
晚上,他也时常带我去街上喝酒。
大街上有这么一间两张半边桌子的炖货店,卖些让我流口水的炖牛肚,以及各种烧卤酱肉。隔壁是酒铺。坐定之后,乐平兄照例叫来一小碟切碎的辣味炖牛肚,然后颤巍巍地端着一小满杯白酒从隔壁过来。
他说我听,呷一口酒,舒一口气,然后举起筷子夹一小块牛肚送进嘴里,我跟着也来这么一筷子。表面我按着节拍,心里我按着性子。他一边喝一边说;我不喝酒,空手道似的对着这一小碟东西默哀。第一杯酒喝完了,他起身到隔壁打第二杯酒的时候,机会来了,我两筷子就扫光了那个可怜的小碟子,并且装着这碟东西像是让扒手偷掉那么若无其事。
他小心端着满盛的酒杯,待到坐下,发现碟如满月明光,怆然而曰:“侬要慢慢嚼嘛,嗬!”
然后起身,走到炖锅旁再要了一碟牛肚。他边喝边谈,继之非常警惕我筷子的动向。
事后我一直反复检讨,为什么不拉他的老伙伴陆志庠而拉我陪他喝酒呢?一、他受不了陆志庠的酒量;二、他受不了陆志庠的哄闹脾气。
带我上街的好处如下:
一、我不喝酒,省下酒钱。二、虽然有时筷子节拍失调,但是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弟。三、我是个耐心聆听的陪酒人。四、酒价贵之,肚价贱多,添多一两碟,不影响经济平衡。
到了星期六,雏音大嫂要到几里外的虎岗儿童新村托儿所去接孩子。现在我已经糊涂了,到虎岗接的是老二小小,那老大咪咪是不是在城里某个托儿所或幼儿园呢?
我没来赣州时,陪雏音嫂去虎岗有过好多人,木刻家荒烟啦!木刻家余白墅啦!木刻家陈庭诗啦!到后来剩下陈庭诗去得多了,我一来,代替了陈庭诗。陈庭诗是个重听的人,几里地路上不说话是难受的,何况我喜欢陪雏音大嫂走东走西,说说话,我力气大,一路抱小小胜任愉快。
那里托儿所办得好,有条理,制度严格。有一次去晚了,剩小小一个人在小床上吮脚趾头。办手续的是位中等身材、穿灰色制服的好女子,行止文雅,跟雏音大嫂是熟人,说了几句话,回来的路上雏音嫂告诉我,她名叫章亚若,是蒋经国的朋友。听了不以为意,几十年后出了这么大的新闻,令人感叹!
乐平兄胆子特别、特别、特别之小,小到难以形容。雏音嫂觉得好笑,见多不怪,任其为之。
飞机警报响了,我和陈庭诗兄恰好在乐平兄家里聊夜天,九点多十点钟,他带着我和庭诗兄拔腿就跑。他的逃警报风采是早已闻名的,难得有机会奉陪一趟。他带路下坡,过章江浮桥,上坡,下坡;再过贡江浮桥,上坡,上坡,上坡,穿过漫长的密林来到一片荒冢之中,头也不回地钻进一个没有棺材的坟洞里去。自我安顿之后,急忙从坟洞里伸出手来轻声招呼我和陈庭诗兄进去,原来是口广穴,大有回旋余地,我听听不见动静,刚迈出洞口透透气,他蹩腔骂我:
“侬阿是想死?侬想死侬自家嘅事,侬连累我格浪讲?快点进来!”
我想,日本鬼子若真照张乐平这样战略思想,早就提前投降好几年了。漠漠大地,月光如水,人影如芥,日本鬼子怎么瞄得准你张乐平?他专炸你张乐平欲求何为?
后来才听说他胆小得有道理。在桂林,他跟音乐家张曙、画家周令钊和家人在屋里吃晚饭,眼看炸死了身边的张曙。怎么不怕?
雏音嫂带着孩子在家里,稳若泰山,好不令人感动。
后来我到赣州边上的一个小县民众教育馆工作去了。陆志庠在附近南康。日本打通了湘桂线,把中国东南切为两半。麻烦来了。
不到一年,日本鬼子占领赣州,宣布扫荡三南(龙南、虔南、定南),追得国民党余汉谋的七战区大兵四处逃窜。真正是搞得周天火热。
逃难的比赶集的还热闹。这当口,谁都有机会见识日本兵未到、中国人自己糟蹋自己的规模景象了。说出来难以相信,在同一条道路上,混乱的人流有上下好几层,灾难是立体的。
我逃到龙南,遇见陆志庠兄,他说乐平兄和雏音嫂也在,我问:“孩子呢?”他说:“平安!平安!”。
马上去看他们,原来在摆地摊,卖他们随身带着的衣物。乐平兄打着赤脚卖他那双讲究的皮鞋。
又碰见画家颜式,还有小高。
后来读到朋友写的回忆文章,说他们跟陈郎几个人开小饭店,我怎么不晓得?可能我还在信丰没赶上吧。有一天乐平兄异想天开,做了满满一缸炎夏解暑去火恩物——清甜藕粉蛋花汤。做法简单,煮一锅开水,打两个鸡蛋下去,放二两山芋粉一搅,加十几粒糖精即成。本小利厚,一碗若干钱,几十碗,你说多少钱?几十万逃难的,一人一碗是什么光景?一人两碗又是什么光景?东西做好,来了场瓢泼大雨,早上七点下到下午五点多,别说人,连鸭子也缩回窝里。天气闷热,眼看整整一聚宝盆妙物付之东流,便大方地请陆志庠、颜式和我痛喝起来。如果我是过路难民偶然来一碗喝喝,未尝不是解渴佳饮;但好端端坐着的三个人要一口气把整缸东西喝完,那就很需要有一点愚公移山的精神了。乐平兄还问我们:
“味道哪能?崭哇?”
颜式这人狡猾,连忙说:
“一齐来!一齐来嘛!叫阿嫂、孩子都来喝……”
陆志庠不知天高地厚:
“侬叫我伲光喝液体,也唔俾点硬点嘅实在物事吃吃,——残忍!”
后来听说这缸东西真倒进街边沟里去了。其实早就该倒,免得一半装在我们肚子里。
不久乐平兄一家搭便车走了。记不得是去梅县还是长汀。总是这样居无定所,像大篷车生涯浮浪四方。我们送车,他在卡车后头操着蹩脚京片子叫着:
“黄牛黄牛!年节弗好过,你赶到××找我伲!”(我诨名叫“黄牛”。)
车子太快,偏偏××两个字没听清楚……
再见面是一九四七年的春天了。
三毛在《大公报》连载,受到全国人民的爱戴。那时天气冷,三毛穿的还是单衣,女孩子们寄来给三毛打的小毛裤毛衣,而在画上,三毛真的就穿上这些深情的衣物。这些衣物也温暖着病中的乐平兄。
他住在几马路卖回力鞋之类铺子的二楼,在吐血。与人喝酒闹出来的。雏音嫂和孩子在嘉兴,不晓得知不知道。
有时碰碰头,陪他吃小馆子,喝酒。在那段时候,我没见到雏音嫂和孩子。听说他俩添了许许多多儿女,并且又收养了许许多多儿女,一个又一个,形成张冯兵团的伟大阵容。设想生儿养女的艰难,便明白这一对父母心胸之博大,他们情感落脚处之为凡人所不及。
一九四八年我离开上海经台湾到香港去了。再见乐平兄是在一九五三年的北京。他到北京开会,当然我们会在一起聚一聚,吃一点东西,喝喝茶。“相濡以沫”嘛!等到一搞运动,便又“不若其相忘于江湖”,这么往来回荡,轻率地把几十年时光渡过了。
人死如远游,他归来在活人心上。
我有不少尊敬的前辈和兄长,一生成就总有点文不对题。学问渊博、人格高尚的绀弩先生最后以新式旧诗传世,简直是笑话。沈从文表叔生前最后一部作品是服饰史图录,让人哭笑不得;但都是绝上精品。乐平兄一生牵着三毛的小手奔波国土六十多年,遍洒爱心,广结善缘,根深蒂固,增添祖国文化历史光彩,也耗尽了移山心力。
我是千百万人中乐平兄的受益者之一。从崇拜他到与他为友半个多世纪,感惜他还有许多聪明才智没有使用出来。他的长处,恰好是目下艺坛忽略缺少之处。古人所谓“传神写照”,他运用最是生动流畅。不拘泥于照片式的“形似”,夸张中见蕴藉,繁复间出条理。……要是有心人作一些他与同行闲谈交往和艺术创作时的记录,积少成多,可能对广大自学者如我辈是一部有用的自学恩物。
乐平兄有许多令人意想不到的精彩到家的巧思和本领。
一次在北京张正宇家吃饭,席上吃螃蟹他留下了壳,饭后他在壳盖纹路上稍加三两笔,活脱一副张正宇胖面孔出现眼前,令人惊叹!
熟朋友都知道他能不打稿一口气剪出两大红白喜事队伍,剪出连人带景的《九曲桥看乌龟图》。他的确太忙,这一辈子没有真正地到哪里玩过。去外国也不多,随的是代表团,难得尽兴。要是他健在多好!让我陪着他和雏音嫂、绀弩、沈表叔、郑可诸位老人在我意大利家里住住,院子坐坐,开着车子四处看看、走走多好!这明明是办得到的,唉!都错过了。年轻人是时常错过老人的。
一梦醒来,我竟然也七十多了!他妈的,谁把我的时光偷了?把我的熟人的时光偷了?让我们辜负许多没来得及做完的工作,辜负许多感情!
1997年7月22日于上海
--摘自《比我老的老头》,作家出版社2003年7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