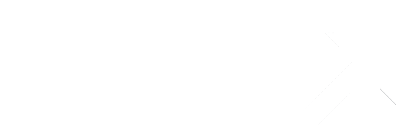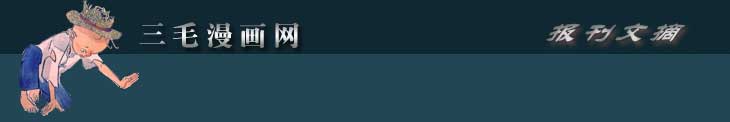
往事历历
戴敦邦
三毛之父——张乐平先生离开大家已经十年了,他呕心沥血创造的“三毛”已成为家喻户晓深入人心的艺术形象。在广大的读者群中,不少是因热爱“三毛”而走上绘画事业的,我即是众多之中的一个。我对三毛的如痴如醉可以说到了癫狂的地步。《三毛从军记》、《三毛流浪记》、《三毛外传》等画集,我是用不吃早点积攒的钱买来的。自己的绘画能力亦是从一笔一划地临摹三毛而入门的。所以从少年时代起,张乐平先生就是我心目中无限崇拜的老师。记得那年“三毛展览义卖”设在大新公司,我从老远的家里步行至大新公司,只见从低层排队至四楼,在楼梯过道处黑鸦鸦一片都是一些和我同龄的观众。那次我只是远远地瞥见了在涌动的人潮中的三毛之父一眼。在我读初二那年参加了一次张乐平先生与读者的座谈会,地点是绍兴路口那座小洋房里,好像是美协的创作室。会议是张先生听取读者意见,我无心听与会者的发言,只是一门心思地观看张先生的一举一动,只觉得三毛父亲的年纪不是想象中的老。张先生一袭藏青卡其布中山装棉袄,显得干练而精神。对大家的意见都逐一在自己的笔记本上认真记录着。记得会后我们几个学生围住了张先生,请他在自己的本子上签名并画三毛。张先生一一满足要求,我是最后一个轮到,前面都是其他学校的女生,她们均拿出了十分精致的大笔记本,我只是手掌大小的日记本。但张先生一视同仁,均一一认真画来,每个三毛都是不同样的,有戴红领巾、有戴帽的,亦有正面和侧面的,不重复充数,且根据构图签名和写日期。我深深感受到这样一位被读者敬仰的人竟是如此平易近人。
几年后我在一家儿童杂志当美编(其实是名跑腿的),任务之一是到名画家中送稿、取稿。张乐平先生家是我跑得最多的一位, 几乎是隔三差五就得上张家一次。《咪咪画传》是张先生除了画三毛和其他人物故事外,为少儿读者精心绘制的一套以猫咪、老鼠等动物为内容的彩图长篇连载。绘制儿童读物的作品,最可贵的是一片纯真的童心和童趣,这些绝非是简单的外形夸张和噱头可以换取的。当时张先生的每一构思都主动与编辑部切磋商量,乃至数易其稿,绝非大笔一挥而就。当年我经手连载《二娃子》(郑拾风配诗),有机会经常站在他画桌边看他从起稿到勾线完成,擦橡皮到掸灰。他画任何造型形象都成竹在胸,可谓得心应手。有些人物生动的动作,他却从脚趾头画起倒画至头部,总是先把肢体中生动的关键部位先画就,这是绝顶的功夫。张老师对我一点不卖关子,有时他画完后也会要我替他擦橡皮,我是极其乐意尊命的。一件刚完成的作品我为自己能成为第一个读者而激动,我可以如此亲近原稿仔仔细细地拜读,从中领悟其所以然,机会难得,我常因惶恐不小心擦脏了画面,张老师会在我疏漏之处补擦一遍。这种认真对待创作的每个细节不仅是对自己亦是对读者的负责。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张乐平老师就作为第一批“牛鬼蛇神”被揪出来了。从此他被剥夺了手中的画笔,整天拿着扫帚拖把在解放日报大楼内打扫卫生。这是心灵和人格的摧残和侮辱。那天我与张老师在十七路电车内相遇,在拥护的车厢内彼此紧紧地拥抱,只能深沉而复杂地说了一个字“好?”“好!”彼此强忍着,大丈夫有泪不轻弹。十年不堪的日子总算挺过来了。“文革”后期,张老师从五七干校的老虎灶中被解放回家了。我也挨过了因画样板戏连环画而遭的厄运。我又常在张老师家泡辰光。一日我向张老师提出请他在我的砚盖上画一阿Q造型并镌刻以志永念。这由头是因为友人曾秘示过我一套张老师为大公滑稽剧团绘制的《阿Q》全剧的人物造型图,不仅十分到位地诠释了原著精神乃至细节,而且将剧中人与扮演者的生理特征融为一体,不由你不拍案叫绝。我原原本本地诉说着看图的经过,讲述画面上的每个细节,并提出了在当时看来极为荒唐的请求。这似乎勾起了他当年创作所带来的振奋,竟然慨允了。当我手捧那砚盖上张老师的亲笔画就的阿Q而激动时,张老师低沉地对我说:“一家性命都交给你了……”
“文革”终于熬过去了,大家大画特画打倒“四人帮”的漫画,不免要助兴地喝上几杯。酒更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劫后余生,南来北往的画家开始走访,张乐平先生的家也是必到之处。当时大家手头不宽裕,饭店酒肆不多,因此待客多半在家中弄点熟菜和零拷些酒水。有时我刚巧在场,在张老师的示意下,两人拎了竹篮再端个钢精锅子到附近的餐厅去外买几色炒菜和零拷一锅子鲜啤待用。也就在等候出菜之际,两人把已拷在锅子里的啤酒先喝开了,所以当酒菜拿回家时,两人肚内与锅里都盛满了啤酒。朋友们也看出了这极具漫画风格买菜待客之道,相视而笑。
“文革”后的第一次全国政协开大会,张老师恢复了政协委员身份到京参加大会。全体委员下榻于北京友谊宾馆,其时我正在北京绘制英文版《红楼梦》插图,也住在该宾馆的大院内。那天因赶画而错过了餐厅的开饭时间,只得挨饿过夜了。适时张老师来电话要我去他那里。入得房内,见张老师换了一身新制的米褐色的卡中山装,容光焕发,颇有兴致并利索地从公文包里取出个纸包,打开只见是油炸大虾,还捧出了一瓶“二锅头”,又找出些花生米。张老师告知大虾是宴会上带回的,要与我有福同享,在那年月能吃上大虾当然是享福了,但我更感受到老一辈对自己的关爱至深,那滋味永存至今。
晚年的张乐平老师疾病缠身,影响了他的艺术才华。他与我谈得最多的是如何变法,创作新作品,乃至突破画种局限的问题。虽然张老师住院接受的是最好的治疗,但我去医院探视他时,他说的最多的是如何想画画,他颤抖的手从身边摸索出一个小本子,上面密密匝匝记画着种种创作设想,又陪我参观了经医生同意提供的作画场所,那是个仅可安置块木板的地方。老艺术家强烈的创作欲和如此的环境,使我心酸。张老师最后躺倒在病床上不能说话也无表情,我想他一定是在默默地思念并惦记着他的创作、三毛、家人、朋友和后辈们。他生前曾嘱咐过:他最喜爱《一路平安》这首曲子。因此追悼会上一曲《一路平安》,使我领悟了张老师的良苦用意。
张乐平老师走了,一位“知足常乐”、平易近人的画坛大师,被大众传诵的三毛之父走了。他毕生辛勤,付出了艰巨的艺术劳作,他坎坷的一生却为人们留下了无法替代的艺术硕果。
三毛永存,老师永存!
——摘自2002年10月20日《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