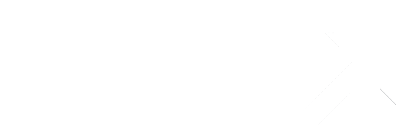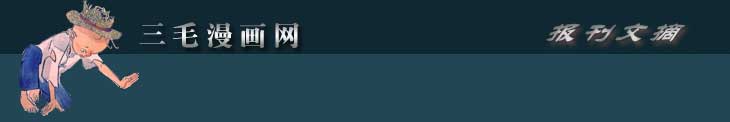
一生中最温暖的日子
编外儿女追忆张爸爸
刘琳 徐平
在上海西区幽静的五原路上,有一座小楼仿佛总与孩子有着不解之缘,那就是诞生三毛的张乐平的家。在这个家里,不仅成长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孩子的朋友——三毛,还有七八个孩子在这里留下了一生中最温暖的回忆。这些孩子在张乐平、冯雏音夫妇人生的不同时期成了他们的“编外”儿女,与他们一起经历了一场又一场命运的考验。
这是张乐平夫妇几个“编外儿女”讲述的他们在张乐平身边的鲜为人知的故事。
熊根发的故事
我的一生颇富传奇色彩:做过拖拉机手,画过漫画,写过散文,蹲过大狱,编写的美术片获过奖,现在又是个专利发明者,远近闻名的富裕户。
在我起起落落的一生中,有一个场景无数次地出现在我的梦中,闪回在我的脑海里。那就是:一个爬在铁门上小男孩被一双大手轻轻抱下,那双大手又轻轻抚过小男孩的短发,叮嘱道:“小心,有危险哦。”
那个小男孩就是我,那双大手是爸爸的手,张乐平爸爸的手。
我的亲生父亲原是一位英国侨民,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日军关进了集中营,从此便和我们母子失去联系,不久,母亲也离开了我,我成了一个孤儿。
1955年的一天,正当我因住宿问题就要中途辍学的当口,我的同学、张爸爸的长子张融融伸出了援手。那时,融融家虽说有五六间房,可十几口人住也不算宽敞。
但当融融把我的故事告诉张爸爸后,张爸爸与张妈妈急急地商议一下,决定腾出三楼的一个小间让我住下。
从此,我成了张家的正式成员。那时正逢全国风行大跃进,张爸爸在《解放日报》的工作特别忙,几乎每天都有时事漫画见报,为此,他常常工作到深夜。而我,每天晚上,悄悄地在灯下为张爸爸磨墨倒水,看他的笔下如何生出一幅幅妙趣横生的漫画。时值深冬,我因为没有厚衣服冻得瑟瑟发抖,张爸爸又将自己半新的羊毛衫和丝棉棉袄披到了我身上,让我安然度过了寒冬。那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
后来,我考取了可以住校的七宝中学,可每逢周末,我仍然像其他有家的孩子一样,回张爸爸的小楼住上一天。
念了一年初中,我的经济状况越来越窘困,我想我再也不能给本来就多子女的张爸爸家添麻烦了。于是,我决心退学。我瞒着张爸爸,张妈妈,独自一人偷偷地来到建筑工地打工。一个月后,当我拿着用第一次挣来的工资为张爸爸买的他最嗜好的酒,回到小楼时,张爸爸和张妈妈既心疼,又欣喜。
后来,我迁到了邯郸姨妈家,我时常给他们写信,寄去我在报上发表的漫画。不久,“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我因为是“保守派”,被“中央文革”点了名,被投入监狱,与外界完全隔绝了。几年后,当我重获自由,我第一件事就是带着女儿回到上海,直奔日思夜想的小楼看望爸爸、妈妈。
我无法忘记那座小楼,那里有轻轻抚过头发的温暖的爸爸的手。
江圣行的故事
我第一次到张爸爸、张妈妈家时才五六岁。那时,我的父亲江寒汀,一位颇负名望的国画家,是张爸爸的好朋友。我们两家离得很近,50年代初,这对酒友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两人你来我往,品酒论画,煞是投缘。
而我,我和张爸爸的小女儿,与我年龄相仿的朵朵成了同学和知心朋友。那时,我和朵朵都迷上了越剧。一放学,朵朵的家就成了排练场,两人在镜子前咿咿呀呀地唱,朵朵的外婆也是个越剧迷,常常来为我们捧场,我们两人闹得更有劲了。有一次,两位“演员”关紧房门,把沙发上、床上的毛巾、被罩全部披挂在身上,好戏刚开场,冷不防张爸爸下班回家推门而入,他连连惊呼:“哪里来了两个小妖怪!”只要张爸爸有空,就会来观赏我们两个小姑娘的表演。
一转眼,我和朵朵都成了十六七岁的大姑娘,再也没有那份唱越剧的热情和疯狂,但我深深爱上朵朵的家庭。那时,朵朵决意奔赴新疆建设兵团。临行前,她拉着我的手对张妈妈说:“妈,我走了,请圣行代我照顾你,你就认她做干女儿吧。”张妈妈当即拿出自己的一件羊毛衫和一条呢裙作为认亲礼,收下我这个干女儿。
朵朵走后,我仍然常常到张家,和张妈妈、张爸爸聊天拉家常,他们鼓励我拿起父亲的笔,也试着做一名画家。然而,我的画家梦还未能实现。在一浪高过一浪的上山下乡洪流中,我也终于被推上了奔赴黑龙江的列车。
如今,我也为人母,张爸爸、张妈妈家里那种鼓勋孩子发展兴趣的氛围也成了我家庭教育所追求的目标。
灯灯的故事
每次出差到上海,在北京上火车的时候,我便会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我又踏上了回家的路。在那里,我不是建筑摄影家韦然,而是灯灯。
说起来,三毛爸爸与我家的渊源很深。张爸爸曾在解放前与我的母亲上官云珠合作拍过那部著名的《三毛流浪记》,影片中亲吻三毛的那个讨人喜欢的小姑娘是我的姐姐姚姚。说来也巧,我的奶妈又是张爸爸的三子苏军的奶妈,因为我和阿三是奶兄弟,关系好得自不必说。而我的姐姐姚姚又与张爸爸的二女儿晓晓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50年代,我去了北京祖父家,当我再回上海时,已是个瘦瘦的小伙子。然而,生活中最残酷的打击接踵而来。短短10年间,我的母亲上官云珠和叔叔、姐姐等相继去世。而且没有一个属于正常死亡。我的生活陷入无尽黑暗之中。
正当我近乎绝望的时候,是张爸爸、张妈妈把我留在他们那里,开导我,劝慰我,细心照顾我。张爸爸还教我学画,让我千万别浪费难得的艺术资质。是张爸爸、张妈妈弥补了我失去的亲情,让我重有勇气去面对生活。
那是一段难忘的非常岁月,也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日子。
现在,我又回家来了。我知道,只要打开那扇熟悉的铁门,我就打开了一扇永远欢迎我的家门。
杜民元的故事
我家和张家是近30年的老邻居。小时候我只知道张爸爸就是那个画出三毛的人,是个不起的画家。而我却是一个读书不多,工人家庭出生的孩子。
然而,张爸爸、张妈妈却从来没有半分的嫌弃或轻视,而且总将我当作自家的孩子。送衣送鞋,问寒问暖,有空的时候,张爸爸还要拉我喝两杯,聊聊天。令我最难忘的是,在我结婚前,一个下雨的早晨,病中的张爸爸特意拄着拐杖从医院赶回来,为我画了一幅三毛图作为给我结婚贺贺礼。那天,我心中所涌起的感动是无法言表的。
后来,张妈妈忽然从神经官能症转化为更年期瘫痪,成了一个不能动弹的人。而他们的儿子三班连轴翻,喂张妈妈吃饭的事成了难题。我想,到了该我回报爱心尽责任的时候了。于是,我挑起了天天喂张妈妈吃饭的重担,一干就干了一年多。
如今,张妈妈在人前人后总要提起她瘫痪在床的日子我对她照顾,其实,我只是把张爸爸所言传身教的回报给这个家庭。
——摘自1996年4月16日《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