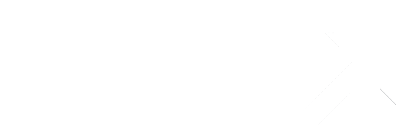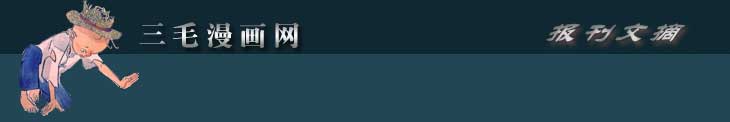
从《三毛流浪记》的“恐吓信”说开去
韦 布
1948年夏秋之交,漫画艺术家张乐平创作的连环画《三毛流浪记》被我看中、选定,经过协议签字取得了版权,准备把它搬上银幕,当时,上海的电影刊物、小报等都传播得满城风雨了。在我们正紧张筹备,即将开拍之前,突然,张乐平接到了一封无头无尾的警告信,信上写着:“不准将三毛搬上银幕!假如不听的话,将予以不利!”同一天,我也收到一封恐吓信:“三毛再搞下去,当心脑袋!”
当时,我刚刚当上所谓独立制片人,这种人应该既是企业家又是艺术家,而我正在学着起步,并且抱着一番雄心。从给我的恐吓信上的口气看,有脑袋问题,比起张乐平来似乎更严重一些。不过,《三毛流浪记》的拍摄,并未因这两封匿名恐吓信而受丝毫影响,恰恰相反,我们这一撮要拍《三毛》的哥儿们,反到更加鼓起了斗志对着干!
接到怪信的第二天,乐平和我在聚会中把情况平平淡淡地和大家谈了。有意思的是,筹划《三毛》拍摄的“难兄难弟”们,听到这个意外的显然是政治恫吓的信息后,反应很一般,谁也没有表露惊慌退缩的不安情绪,而是像上海话说的:“象煞呒介事。”直到影片完成,也都一直“象煞呒介事”。所谓恐吓信,倒可以说真的只是“恐吓”一下而已。不过此事从当时的具体情况来说,确实也反映了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让我们又一次领教了反动派的拙劣与无能,已经近乎无聊了!
我着手准备拍摄《三毛》的那年是1947年。以前,我和虞哲光、张友良、蒋柯夫、周伯勋等朋友一起经营虹光戏院,想为“新中国剧社”在上海立足作些准备,可是,在那百业萧条的年月里,我们的剧场梦破灭了,但是,从天天接触的电影中引发了我投入电影圈的动机。这样,在妹妹的资助下,我放弃了十几年的戏剧生活,当上了独立制片人。
触电后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我拍摄什么影片呢?我以自己十多年的生活实践和“社会大学”积累的理论与感情,选定了第一批制片的三个题材:1.三毛;2.鲁迅的童年;3.吉诃德爷爷(根据堂·吉诃德故事改编,全部由儿童演出的中国化的喜剧和舞剧)。我的奋斗目标是当一个儿童电影艺术家和制片家。
首先,着手接触《三毛》。关于此剧的初衷,我借用夏衍同志于1950年在张乐平《三毛流浪记》(选集)所作代序中的话:“三毛是上海市民最熟悉的一个人物……三毛的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所以在解放前那一段最黑暗的时期之内,作家笔下的三毛的一言一行,也渐渐地从单纯的对弱小者的怜悯和同情,一变而成对不合理的、人吃人的社会的抗议和控诉了!”夏衍同志的话虽是在影片完成之后说的,可也说到了我们“三毛摄制组”全体同仁的最初的心里,完全点出了我最早选定它搬上银幕的着眼点。
决心下定,马上展开工作,我先找了陈鲤庭,请他出任《三毛》的导演。他曾是我江阴家乡高小里出类拔萃的同班同学,一直是我所敬佩的人,心里暗暗以他为师,拍电影自然第一个就想到了他。遗憾的是,他正着手《丽人行》的拍摄工作,无法抽身,但他答应介绍合适的人,并指点道:影片的成功,关键在于剧本,可请阳翰笙编剧。他亲自去说。又指出拍摄工作的第一步,要取得搬上银幕的版权,命我通过冯亦代帮助解决。亦代是我在重庆跟鲤庭演出《大马戏团》时熟识的朋友,靠他的热情相助,我很快便和张乐平订好了协议书,取得了《三毛》的版权,随后,鲤庭又推荐赵明、严恭担任导演。他们也早就和我相识,特别是严恭,是我在桂林新中国剧社时的老朋友,他们二人都是抗战胜利后由党组织调到电影界跟鲤庭和应云卫拍摄影片的。之后,我找了阳翰笙同志,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从最早认识他到今天,我们都尊称他翰老。1986年,翰老在《泥泞中的战斗》一文中曾写道:“《三毛流浪记》是我编写的……最早是韦布来找我,告诉我,他想搞个剧本,他还找了冯亦代。我说,漫画《三毛》不是一个连贯的故事,要写剧本必须重新结构。我当时想,如何在漫画《三毛》的基础上将主题深挖下去。电影剧本必须重取其精华……”
当时,我和赵明、严恭等等追随着翰老,围绕着剧本的创作工作而转。凭翰老的威望和写作经验,完全可以搬开我们这几个毛头小伙子,把剧本写完交给我们就行了。但是,他却表现出了高度的民主作风。他要我们搜集了所有《三毛》漫画的材料,一起浏览,他随时发表一些意见。在动手写之前,翰老先把将如何写的方案告诉我们,同时征询大家的意见。写作中当每一场戏或情节告一段落的时候,就把初稿给我们传阅并听取意见……
翰老当时是刚建厂不久的昆仑公司的编委会主任。昆仑是在国统区唯一的地下党领导的电影厂,当时局外人是不知道的,仅知它是一个比较进步的厂。翰老的工作十分繁重,写《三毛》是在很紧张的时间中进行的,有时只好为他租一个旅馆的房间躲起来写作。他经常还参加昆仑其他剧本的创作活动,印象最深的就是经常约在晚上在湖南路任公馆里聚会,热烈讨论。工作之余,又常打开收音机听解放区广播电台的新闻,那真够劲儿!参加这种聚会的人还有:陈白尘、郑君里、王林谷、赵丹、徐韬等等。
在创作剧本的同时,我们的筹备工作已经有了个大致头绪。摄制组主创人员基本都是双方乐意合作的,大家艺术倾向相投,有默契、有共同语言。两位导演化了很大功夫找到王龙基来扮演三毛,他是作曲家王云阶的公子,当时才九岁,聪明伶俐,也很顽皮,能吃苦。凡是看过影片的人,都认为他的表演是成功的,留给观众一个难忘的可爱的印象。
由于题材所决定,三毛必须接触各种阶层的众多的人物,所以大人角色有名有姓的就有三、四十个。我对所有的电影演员,有特别的爱心和尊敬。特别值得一说的是,在戏里“贵妇人为三毛做生日”这一场的讽刺喜剧场景中,男女宾客有四、五十位之多,参加演出的演员大多不肯领取酬金,他们是闻风而主动来参加扮演“群众”的影剧界的大演员、大明星,这种情况当时在电影界是破天荒的。因为有特殊的历史意义,我不能不写下他们的大名:中叔皇、王静安、朱莎、朱琳、沙莉、阮斐、林子丹、金淑芝、吴茵、林默予、奇梦石、徐曼、徐缓、袁蓉、孙道临、高正、郭玲、黄宗英、黄温如、梁明、高依云、许蓝、章曼苹、张劭、张乾、张婉、张逸生、傅惠珍、张庆芬、程梦莲、农中南、赵丹、汪漪、熊伟、关鹏、应萱、蓝优心、苏英、苏茵、苏曼意、谭云、上官云珠、姚姚……
这样一张名单,我郑重其事的再公之于世主要用意在于第一,针对反动派特务的“恐吓信”再给予迎头痛击!第二,《三毛》一片纵然够不上称为经典作品,然而就凭这部戏的其中一个群众场面,承蒙这么众多的熠熠发光的明星群赏脸光临,济济于一堂,真是“空前绝后”的事情!当然,从中也可以想见当时我们中国的政治气候:蒋家王朝即将倾覆,人民当家作主的黎明已呈现曙光了。同时也荣耀地证明《三毛流浪记》总体没有脱离时代,没有脱离生活,也没有脱离群众,因而才得到电影界同行的支持。
我特别想说的是我得到两个妹妹的帮助:一个是韦丽琳;一个是上官云珠。她们俩都曾热情、真诚的大力支持了我拍《三毛》。韦丽琳在经济上无条件的支援了我。至于上官云珠对我的支持帮助,达到了把这部戏的一切工作,当成了她自己的工作的程度。她还带了她唯一的宝贝女儿姚姚一起参加拍戏,一连几个通宵没有半句牢骚,没有拿一分钱。照我们家乡的称呼,她们都叫我“大大”,我叫丽琳为“阿宝”,叫上官为“亚弟”,她们都不幸先后含冤横死了,连姚姚也意外不幸的死于车祸。现在只能在《三毛》电影中看到她们三个可爱的倩影了。每想到这里,实在无法抑止我心里的无比悲伤。
这部电影就我个人来说,从筹备到拍摄前的准备,都是我一个人以独立制片的方式进行的。在正式跨进拍摄之前,有一天,翰老特地找我谈话,他指出:拍摄工作和后期阶段中,人力、物力、财力等条件都非常困难,如摄影棚、摄影器材,特别是胶片来源、洗印以及配音乐……等等都不是单枪匹马或光靠钞票就能够轻易解决的。他代表昆仑公司,要我把《三毛》这个剧目以及已组成的摄制组全班人马都加入昆仑公司,已经完成的多项工作,当然也都带到昆仑公司去,总之,把这部影片作为昆仑的出品之一。
我单独一个人搞下去,当然困难重重,这是我早就估计到的,但却已下决心闯到底的,而且还梦想当一个专拍儿童电影的独立制片人,还计划着开拍《鲁迅的童年》和《吉诃德爷爷》呢!但是翰老的谈话,以我与他的关系,他的地位、身份和他所讲的道理,还有昆仑公司这个具体形象,我确实没有任何理由拒绝他。这样,从1948年8月份开始,《三毛》成为昆仑的一个剧目。我们几个主要人员从8月份开始编入昆仑的花名册,领取昆仑的工资。在这之前,我经手已支付的费用,包括购买版权的费用在内全由昆仑公司陆续付还给我。版权协议书也通过我和冯亦代征得张乐平的同意,由昆仑公司保证应尽的义务和责任。然而,后来有朋友好意的指出:昆仑公司出品是进步的,但老板们到底还是资本家,他们大鱼吃小鱼,要去了这个剧目,除当然应该付还我给张乐平的版权费外,还应该另外付给我一笔转让这个剧目的经费;而且昆仑接收过去我们已经开支的账目中,我们几个主要工作人员都没有支付过工资,但实际上已做了许多工作,应该由昆仑老板补付这些工资。最重要还有笔糊涂账,就是当初与张乐平签订的版权协议中,有影片在国际发行的收益中,必须给原作一定的分成……所有这一切都不了了之。我们这些人到底还是穷秀才,只有吃亏的份。事情过去已将近半个世纪了,我们没有要算旧账的意思,但作为电影制片的经验教训之一,值得记取。
《三毛流浪记》开拍,租借了“中电三厂”的场地,也得到徐苏灵大力支持。我算是该片三个(另两人是任宗德、夏云瑚)制片人之一,并兼该片的制作主任。自始至终,我经历了该片制作的全过程,遍尝了甜酸苦辣,永难忘情。
——摘自1993年第1期《电影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