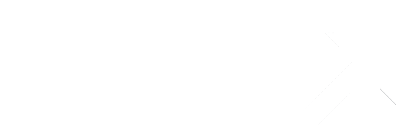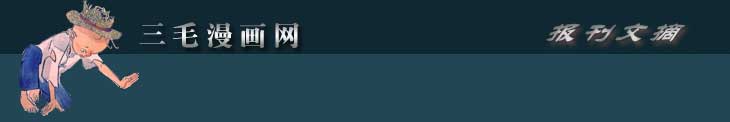
画留天地间 名垂万世后
——忆“三毛爷爷”张乐平
许 寅
1992年11月3日,夜半,自郑州返沪途中。车声辘辘,忽忽若有所思。车到徐州,下车漫步。猛抬头,月色如玉,已过上弦。再一掐指,突然惊觉:此乃何夕?辛未十月初九——如“三毛爷爷”张乐平在世,已八十有三了!一番惘然之后,刹时思潮汹涌,不能自己。
一哭一笑已成永诀
去年大年初一,得知此老病危。一早赶去探望。此时他已无力开口,但神智尚清。一见我,竟紧紧拉住我的手,凄然泪下。张老老生性乐观、幽默,这两滴泪,自然紧紧揪住了我的心。
年初四,我又前去探望。多年来,笔者与丁锡满已经养成一个习惯:每逢春节,总要到张家拜年,共饮一次酒。“三毛爷爷”嗜酒如命。可是久病之身,确实不宜于酒,所以雏音大姐和孩子们都不准他多饮。唯有小丁和笔者在座,才许开禁。笔者好酒而不善饮。小丁能饮,就不仅成了此老最好的忘年交,更成了他的好酒伴。前年初四这天,此老和我们开怀畅饮,情绪甚高。光阴迅速,倏忽一年。现在他正苦苦与病魔争斗于病床。床前唯有爱女朵朵侍候。他神志尚清,一见笔者又紧紧攥住,欲语不能。笔者凑近耳边,高声喊道:“老老!去年今日,我和小丁在你家畅饮一日。今年你暂时不能起床。我留下一瓶好酒,只等你病好出院,再和小丁来陪你吃酒。现在你唯一的任务,是把病治好。”
听这一讲,他马上把手放开,莞尔一笑。——这一笑,事实上便成永诀!新春过后,笔者东奔西走,回来再去看望,他已经认不得人了。
记得几年前,我国女排“三连冠”的时候,一日竟误传噩耗:此老看电视转播,一时激动,心脏病发作,抢救无效,结果却是一场虚惊。当时笔者曾向此老取笑:“老兄已经向阎罗王报过一次到,判官爷已经把‘张乐平’三字从生死簿上一笔勾销。所以,你定然万寿无疆!”而今此老病危,笔者时时想起这段往事——但愿当真的阎罗王把他忘掉就好了。
在华东医院上下的共同努力下,“三毛爷爷”居然身插数管、在昏迷中熬过了春天,又熬过了夏天。入秋,有相当一段时间,此老病情平稳。爱女朵朵因事假过久,回港销假,准备一月后再行归来。岂料9月下旬,病情恶化,岌岌可危。笔者几次前往探望,医生都说已“回天乏术”。笔者与雏音大姐商量,也认为事已至此,不必强留了。只是希望:能维持到国庆以后,让朵朵回来……
9月27日,笔者匆匆了却杭州工作,乘96次火车赶回上海,想最后送他一送。途中,怔忡不安,忽忽若有所失,只能暗暗祝祷:保此老10天平安,不要让朵朵遗憾终身!
不料,一脚踏入家门,大小子长风劈头一句:“张家刚刚来过电话:“三毛爷爷”今天下午6点多钟‘走’了!!”
闻言木然,虽在意料之中,却在希望之外。朵朵遗憾!我也遗憾!
难忘的两个生日
1969年深秋,已是中共九大之后,政治空气略为宽松。早在九大以前,工宣队和造反派对笔者的“背靠背”审查,已经基本结束。也不知怎么一个心血来潮,笔者忽然想到:可以办一个大型墙报,把那些关在“棚”里的“老黄牛”“牵”出来做做“手民”(旧社会称报社排字工人为“手民”),免得他们你批我,我斗你,没完没了。
于是,笔者便向工宣队领导提出了这个建议,并自告奋勇,愿担任“总编辑”。还推荐两位“革命群众”当“副总编辑”——他们今天可都是新闻界大名鼎鼎的人物了:一位是《上海滩》的副主编华将谟,一位是《上海科技报》的副总编辑毛秀宝。另外,又推荐了一位“美术编辑”——张乐平!
就这样,大型墙报出版了。每星期一次,就贴在教育学院大食堂对面的一块大木板上。第一期,经过我辈精心编辑,质量自然很“高”,特别是“老三毛”的那幅大漫画,格外醒目。尽管没有具名,“广大读者”——新闻出版界的朋友们,一看就知道这是张乐平的手笔。
墙报出了一期又一期,从上海出到华漕,每期最引入注目的总是“老三毛”的漫画。是年深秋,“苹减绿,柳添黄,红莲脱瓣”(《长生殿·水宴》语)笔者得知这位大漫画家正年当60,突发奇想:为他做一次大寿。
做六十大庆,在今天自然理所当然,可在那个时候,“老三毛”紧张得头手俱摇。笔者见他害怕,就来个迂回战术:先说服雏音大姐和他们的儿女:“关起门来,给老老做次寿,送送晦气,我知道不会有问题,请放心!”
十月初九,是日也,风和日丽。张乐平一家欢聚,举行寿宴。贺客仅笔者一人而已。席间,主人公依然闷闷不乐。笔者只好频频劝酒。三年多了,“老三毛”被一纸“勒令”吓倒——“张乐平不准喝酒!”今天,自动开禁,三杯下肚,才真正有点高兴。笔者凑趣,敬了两杯:“第一杯,保证你不久‘解放’;第二杯,预祝老兄70大发!”
这两杯酒一喝,此老兴致来了。先是骂了一通两个“最不讲朋友”的“朋友”;然后,流露了一个美好的愿望,问我:“我能不能入党?”笔者回答得斩钉截铁:“能!”果然,弹指一挥,10年过去,正是在他70诞辰之前,上海少儿出版社的党组织决定吸收这位大漫画家入党。小丁和我特地为此事写了一篇大通讯。
十月初九,他打电话找我。到得他家,这位七十老翁却开心得象小孩子过新年一般。一见面,两个共产党人紧紧握手!他第一句话就是:“我盼了二十年了!”第二句话:“被你说着了!”
“我有笔似刀枪”
在开怀畅饮一番之后,此老郑重其事地拿出两幅画——一幅是他的自画象,一幅是“三毛踢足球”:还说“这两幅都是我的得意之作。这个踢足球的三毛,我自己特别喜欢。你也喜欢三毛,就给了你吧。”那幅自画像,倒与平日所见“三毛爷爷”大不相同。平常,此老慈祥、朴讷、亲切,几无锋芒可言。此画是幅半身像:左手一只酒杯,右手一支大笔,笔尖朝上,头发蓬松,双目凝视笔端,满面春风,洋洋得意,还带几分酒意。画上自题“我有笔似刀枪”。笔者一面看画,一面看人,仔细对照,不禁失声大叫:“今日方识‘老三毛’真面目!”此老急问此话何意?笔者乃告“‘我有笔似刀枪’,此画把老兄精神最深处最本质的东西——革命战士的气质画出来了!”他一听大乐,竟然连说:“识货!识货!”
弹指一挥,14年过去,可惜前3年我送此画去请他题诗,准备为他八十大寿写一文章,不料老人不久即入医院,此画也竟从此不见——“只在此室中,纸深不知处”。
不过,这幅画的神态、寓意,却永远刻在笔者心底,永远不会磨灭。
“我有笔似刀枪!”一点也不为过。他老人家在这块多灾多难的土地上度过了整整82个年头。从小学开始,直到昏迷为止,除了“文革”期间被迫封笔,50多年间,他几乎没有放下过自己的笔,而且大多用来“作刀枪”——
二十年代第一次大革命,他略懂人事,拿起画笔,第一幅画就是“打倒列强反军阀”。
三十年代上半期,他笔不停挥,画的主要也是劳动人民的疾苦,对人吃人旧社会的控诉。
抗日战争,打了8年,他那支笔也画了8年——从纸上画到布上,从地上画到墙上,内容基本一样:打倒日寇,解放中国!
抗战胜利了,我们的“三毛爷爷”可没有“胜利”,家累沉重,重病缠身。尽管如此,他仍然紧紧跟上时代步伐,站到了共产党领导的反饥饿反内战的前列。《三毛流浪记》、《三毛从军记》这两部杰作之所以能如此震撼人心,就因为不仅形象十分生动,而且内容紧密切合时代脉搏。
国民党崩溃了,共产党胜利了,已经进入不惑之年的“老三毛”,从自己的切身经历中,看到了希望——自己的希望,社会的希望,民族的希望,国家的希望!笔锋便转到热情地歌颂共产党、歌颂社会主义上。
“三毛爷爷”是1958年进入解放日报的。副总编辑冯岗问他有什么要求,他的回答简单得很:“能够进党报,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我感到很光荣,什么要求也没有!”这几句话,当时普通又普通,但是张乐平同志却发自肺腑,说到做到——不要加工资,不要房子,甚至连应该有的房贴也不要。今天再听听这几句话,真是“掷地可作金石声”。
从此,他便忘我地为党报工作。从插图、国内漫画、国际漫画,直到速写、标题、头花、版面设计,样样都画。“大跃进”时期,报纸宣传任务重,几乎天天半夜派车把他接到报社编辑部,一起商量,确定内容,请他当场挥毫作画。每画一幅画,他总要广泛征求意见:上至总编辑、下至制版工。有一次,一版编辑请他画一幅表现中国人民大无畏气概的画。他先画了一幅,总编辑魏克明看了不满意,要他重画,还说了一句刺人的话:“你们大画家只肯修修补补,不肯大改!”此时已经半夜,笔者在旁听了,怕他不高兴。谁知他回答一句:“推倒重来!”根据老魏意见,援笔立就——一个农民肩挑日月,手牵蛟龙,昂视阔步。大家看了,个个拍手。老魏一看也大为高兴:“好啊!”
1976年10月6日,“四魔”就缚,万方欢腾。“三毛爷爷”一听消息,立即狂喜,一排排“子弹”从笔尖射向了“四人帮”,其快何如!
笔者最后一次请他作画,是在戊辰年岁尾。解放日报为了祝贺南平纸厂厂庆,想送一样“给人印象深刻的礼物”,因此命笔者请他画三毛。其时,他又住进华东医院,体力甚弱。一听解放日报要他作画,二话不说,当场支撑着画了一幅《三毛放炮仗》,交笔者带走。隔了几天,笔者再往探望,他摸摸索索,又取出了一幅《三毛放炮仗》,上面还落了款,说道:“上次手抖得太厉害,画得不好,这两天手不那么抖,画了这幅,比较好。”
张乐平一生以笔为刀枪,为国、为民、为共产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一生“重于泰山”。他的画,必将长留天地间!他的名,必将永垂万世后。
——摘自1993年第1期《新闻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