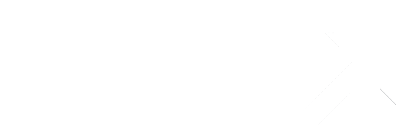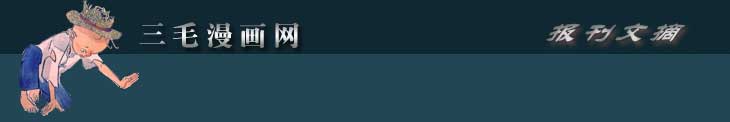
三毛不老
——忆漫画家张乐平
刘连群
一则不过百余字的消息,向人们通报了画家的离去。
望着那对于大师来说只嫌太狭小的篇幅,于无言的痛惜和惆怅中,脑海里蓦然浮起了一幅彩绘的三毛,笑得天真烂漫、逗人可亲,形象是极生动和神采飞扬的,下面却有一个方方正正的“静”字,画与字形成一种既反差又协调的氛围,由于是张贴在医院的白壁上,就越发显得静中有动,使周围含有几许肃穆的宁静、透出了活泼、欢快——或许这才是医院真正需要的静,乐观而且洋溢着生命和活力?
两年前,十月的金秋的一个下午,我去华东医院看望张乐平先生,一进住院部大楼就看见这幅画,走出电梯又见到这幅画,当时想,真是来到三毛之父的身边了,到处受到笑眯眯的三毛的迎接!
来前,一位上海文艺界的朋友告诉我,这家医院距乐平先生的家不远,老人每次患病都来这里住院治疗。于是,三毛随他一起踏进了这静静的白色天地,带来了鲜艳的色彩和笑靥。
像我这样从小对《三毛流浪记》、《三毛从军记》等画册爱不释手,被三毛陪伴着渡过童年,从那一幅幅可笑、可悲、可怜、可叹的画面,依稀感受到画家的善良和爱心的人,到上海是不能不拜访乐平先生的,特别是听到他患病的消息,更急于前去看望。
带小院的两层小楼,画家住在楼上。几间屋的门都开着,一色老式的旧家具,悄无声息。轻轻地敲打两下门板,也不见有人出来,试探着迈进一间大屋张望,发现一位老人仰靠在躺椅上休息,腰间似乎搭着薄毯,浑身洒满暖融融的夕阳。这就是画家了。他终于发觉来了客人,连忙吃力地欠身起来,身材瘦高,长方形脸庞,病容憔悴,满头灰发依然很密,很硬,下面突出的是一只显得厚道而且富于幽默感的大鼻子,眼睛不大,却很生动、有神,使我想起招贴画上三毛那圆圆的黑眼睛。我递上名片和随身带去的《艺术家》杂志,老人接了,一边连连点头寒暄,一边转身寻找什么,我想到是眼镜,他果然举着名片、杂志歉然地笑了笑,又往周围的茶几、沙发上望,没有,就挪动脚步向里屋走。我忙过去搀扶,他并不推让,只顾寻寻觅觅地走。里屋迎面是一张大书桌,整齐地摆放着笔筒、砚台和色盒等用品,还有一叠裁好的纸,好像随时在等候主人挥写;屋角是一张单人床,叠放着被褥,枕头的位置也仿佛时刻准备着老人躺下休息。他去枕边摸,只摸到了一只毛线睡帽。又返回大屋,仍然找不到,显然有点着急,嗓音也越发显得暗哑,吐字困难,但换人时的语调仍是平和的,不带一丝火气。
保姆赶来了,这次她充分尽到了职责,很快把眼镜找到了。老人颤巍巍地戴上,认真地看名片和刊物,脸上漾起了笑意。让我坐,像熟识的朋友那样谈起来。而我,由于多年来通过作品所积累的印象,也许还因为几分钟前亲手馋着老人在屋里转了一圈,身心都没有初到生人家作客的距离感。老人当时八十一岁,十年前患上帕金森氏病,头晕,哮喘,时犯心绞痛,还引发了肺部的隐疾,几度住院治疗,一直没有痊愈,现在不仅手发颤,无法写、画、说话,思维也非常吃力。听着老人暗哑、模糊到难以辨清字音的述说,我的心因同情而沉重起来。但画家的神态还像方才那样平静和舒展。不似一般老年人讲述自己病情时的或痛心疾首,或凄凉无奈,我想这就是漫画大师的境界了。
后来他的夫人和儿子回来,又向我介绍了一些情况。我提出《艺术家》杂志由一个“漫画家作品系列”的栏目,每期发一位画家的作品和创作谈,已发过华君武、丁聪等画家的,下一期准备刊登乐平先生的作品,已经商定请上海的中年画家谢春彦同志帮助整理,老人愉快地同意了,只要求看一看丁聪的文章。我感觉这既是出于对老朋友的关心,也有为自己日后的构思、口述做准备之意,虽然是一篇千把字的短文,作为一位年高名重的老艺术家也是严肃而认真的。
临别前,我想给乐平先生照一张像,并且合影留念,他和家人都爽快地答应了。老太太为乐平先生整理制服上衣,儿子在合影时担任摄影师,发现老人的头发有几绺翘着,就给父亲梳理,怎奈发质太硬,执意不肯平伏,又用热毛巾敷、压,如是者多次,便埋怨起来:“这发总是翘,总是翘……”老夫妇就都开心地笑了。
此刻,照片就摆在我面前的桌上,一只大鼻子,两颗黑亮而且坦然直视的圆眼珠,满头华发虽然全精心地梳向了头顶,但仔细端详,仍可见有几处又不听话、不驯服地翘了起来,使人很容易就想起老人笔下的小主人公,头上那倔强而神气、奇特而著名的标志……老人去了,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会衰老的三毛!
——摘自1992年11月5日《文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