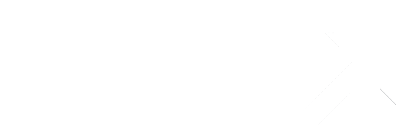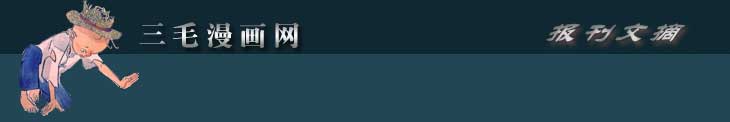
缘悭一面
——忆念张乐平先生
梁兆澄

报载“三毛之父”张乐平先生走完了他80多岁不平凡的历程,安然长逝。阅后怅然。我和张老先生并非深交,仅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缘悭一面,本来是不配写忆念文章的。然而这一面却是印象极深,十多年来总难忘怀,以至不写几个字,怅惘之情,无法排遣。
那是在1977年8月,“四人帮”被粉碎不久,我陪同一群留学英国的香港学生到上海。这些莘莘学子,虽是旅居海外,对国内的文化界知名人士却是非常关切,一到上海,便纷纷要求会见巴金和张乐平两位老先生。当得知他们的要求得到满足时,真是高兴极了。我自然也很兴奋,因为巴金的多本小说以及张乐平先生的《三毛流浪记》我都拜读过,对两位老先生真是心仪已久。“文革”期间他们销声慝迹了十多年,海内外人士关心他们的境况,那是非常自然的。
会见在国际饭店举行,两位老先生一出现,就被这群青年学子包围着,问候声,致敬声,响成一片。许是十多年未曾公开露面,更无接见外宾的机会吧。两位老人显得格外兴奋。坐定后,他们慈祥、爽朗、健谈,对青年们提出的各种问题,都真诚、坦率地有问必答。很快地,两代人就非常融洽地交谈起来。我埋头作着记录,慢慢就感到,两位老先生的谈吐优雅动人,耐人寻味,但又各有特色。巴金老先生的谈话是严谨的、细致的,字字清晰,逻辑性强,记录下来就是一段好文章。张乐平老先生的谈话,却很有《三毛流浪记》的格调。在那本漫画集里,三毛的悲惨遭遇被漫画化了,读者看着看着会笑出声来,但笑声过后,却会感到一种真正的愤怒与悲哀,进而陷入沉思。张乐平老先生的谈话也是如此,对解放前的创作感受和“文革”十年的遭遇这样蕴藏着整个时代的悲伤的话题,谈起来却是那样的幽默,亦庄亦谐,饶有风趣。下面是当时记录下来的张老先生的几段话。
“我解放前画画是为了吃饭,生活是没有保障的,但总比那些流浪的儿童好得多。我要画画,暴露旧社会的黑暗,穷人的苦难,流浪儿的辛酸,就得去了解情况,收集材料。于是我就设法和流浪儿童在一起。这个做起来有困难,旧社会有一种势利眼,衣服稍为好一些,他们就不敢接近你。我起初碰了壁,因为我穿西装。以后我就改穿中装、长衫,而且穿得脏一些,破一些,这样就慢慢同流浪儿童混熟了。结果也闹了一些笑话,因为我穿得又破又脏,一些所谓‘小瘪三’就笑话我,说我是‘老三毛’。我的《三毛》到解放为止,在《大公报》上连载。当时,我自己的生活不很好,但还是拚命画,因为读者需要,一天见不到《三毛》就很失望。报纸的编辑也不放过我。”
谈到“文化大革命”时,他说“他们(按:指‘四人帮’)批判我,我一笑置之,因为我相信将来这些问题总会澄清的。……他们虽然没有打我,但强迫我去干一些力所不能及的劳动,后来因为周围的人看不过眼,提了意见,才改要我干‘轻’活,他们要我在马路上捡垃圾!”“‘四人帮’对漫画是全盘否定的,污蔑为‘臭东西’。每次开画展,都取消漫画的展出,既不准出小册子,也不准见报。……不过,我还是偷偷地在夜间练笔,画些图画,画些鸡呀鸭呀等动物。有一次,我根据毛主席的‘一唱雄鸡天下白’诗句,画了一只公鸡迎着太阳唱。画好后,送给一位朋友把它挂起来,没想到被另一些人看见了,就说‘不得了,你最好赶快取下来,因为你画的公鸡鸡冠不够高,如果被他们看了,会说你讽刺江青的’。但我的朋友不怕,一直挂到‘四人帮’垮了台。”
当说到他和巴金是老朋友了,但十多年都没见过面时,巴金从旁插了话:“我在路上见过你,但不敢打招呼。”张乐平笑起来,说“这样也好,现在见面了,增加了十年的话语,讲也讲不完。”又很高兴地对大家说:“我的《三毛》又翻身了。解放前我画《三毛流浪记》;解放后画《三毛翻身记》;现在画《三毛学雷锋》。”张乐平先生的一番话,使在座的青年们都活跃起来。
在热烈的交谈中,两个小时不知不觉地过去了,我们移位到餐厅,边吃边谈。几位年轻服务员听说张乐平来了,都拿出小白纸请他画个三毛。68岁的张老先生笑呵呵地满足了他们的要求。我趁此机会请张老也画一幅,好送到香港发表,张老很爽快地答应了,约我明天早晨到他家去取。
第二天一早,我如约到张家拜访。张家坐落在一条里弄里,家具和陈设,即使用当时的眼光来看,也是异常简朴的。张老先生很亲切地接待了我,拿出昨夜画好的两幅《三毛》,一幅是《三毛学雷锋》,供发表的,上面还题了几句诗,读上去琅琅上口,诗情画意,浑然一体,生动活跃,妙不可言。另一幅是送给我作留念的。我向张老先生表示了谢意。张老先生又从抽屉里取出印章,郑重地盖在画面上。我注意到这枚印章刻得极好,张老先生笑着说,他的三毛画得多了,看上去一个样,可这枚印章是齐白石老人特意给他刻的,是件真正的艺术精品,他轻易还舍不得用呢。说着,他又指着书架上方挂着的一幅照片,深情地说,他家里最宝贵的就是这帧照片,这是周总理接见他时合照的,他一直悬挂着,可惜周总理逝世了,周总理可真是个好人呵!言罢,宾主都不禁黯然。
接着我请教了一些关于上海文化界的状况后,便告辞了。
回到广州,我把座谈会上的记录整理成文,送交香港一家杂志《新知识》发表,题目是《仲夏访巴金与张乐平》,连同刊登的还有张老的《三毛学雷锋》和巴金老先生写的问候香港同胞的一张条子。几个月后,旅行团的梅女士到广州,她告诉我,由于这篇文章是“文革”后首次以第一手材料较详细地记述两位文化界老人在“文革”中的遭遇和他们的近况,引起香港文化界人士的重视和好评;她又把文章译成英文,在美、英几家杂志转载,一些华侨看到了,反映也很好。
以后我再没有机会见到张老先生,然而凡是报刊杂志刊登的有关他的报导,我总会仔细地阅读。几十年来,像张乐平先生一样,只见过一面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以至难以忘怀的人,是为数不多的。这也算是一种缘分吧。
张乐平老先生笔下的三毛,已成为不朽的艺术形象,“文以人传,人以文传”,’“三毛之父”张乐平老先生也因之而不朽。
——摘自1992年10月23日《广东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