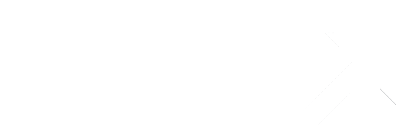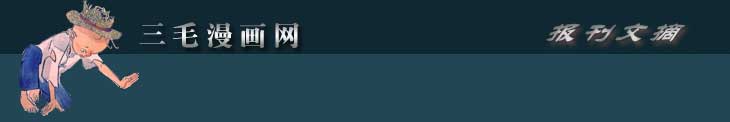
送三毛之父
吴纪椿 陈献珠
他在经历了无数痛苦与欢愉之后,走了。
82年的生命史孕育了一个无与伦比的艺术形象,催生出一种豁达大度的生活力量,现在他走而无憾。
三毛在我们现实中生活了那么多年,我们陪伴着他经历了过去、现在和未来。张乐平这个名字同样也会走向永远。
围坐在父亲的慈像前,儿女们“心曲千万端,想来却难说”。父亲以其博大的爱心超越了人伦之亲。融融的一名同学熊耕发求学时家境贫苦,张乐平夫妇为他提供御寒的毛衣,果腹的食品,常年不辍。小熊外祖父母病故后他成了孤儿,老人索性把他接到家中收养。熊耕发常常当他的助手,后来刻苦自励,学写剧本,在当地很有名气,得到老人格外青睐。小熊常常抽空到上海看望老人,两人亲密无间。上官云珠自杀后,一子韦然一女姚姚生活无着,张乐平常常照顾他们,如同已出。姚姚殁于车祸,老人肠痛寸断。
50年代,美协上海分会提供淮中大楼一个楼面住宅给张乐平,他坚辞不就。他觉得,国家还困难,这么好的房子,要组织上破费不妥当,再说对引导孩子也无益处。他的工资长期没定级而比人少拿,每次加工资他总是先想到同事。一个美术家,纸张和笔墨照例是公家开销的,子女有时想留下几张报销发票,他就婉言制止。融融有时说,你这是老实人明吃亏嘛,他就乐乎乎地说:老实人吃亏?为什么这五个字你们就是想到“吃亏”两个字,而“老实人”这不很好么?
七个子女,后边四个小的,在“文革”中有去新疆的、云南的、江西的,最小的慰军才留在上海进生产组。其他同学全返城后,搞音乐的张建军夫妇一直留在外省。大女娓娓结婚时只有一间九平方米的暗间,二女晓晓儿子18岁了还住在12平方米大的小屋里。对于家庭的这些困难,张乐平从未利用自己的声望去谋私利,爱子之心却深藏肺腑。大女上班,每每因贪觉而误点,他如生物钟到时便轻声呼唤,二女体弱,又常拒绝饮牛乳,他便用牛奶瓶押上一纸条:晓晓,牛奶在此,你为何不吃?孩子们在大漫画家诙谐、幽默的语言环境中潜移默化,精神升华。
父亲尊重人,他以为来家的都是客人。儿女们常常听到这样的教诲:你们对保姆阿姨怎么样?她替你们做事,都得表示谢意唷。在他生命之火即将熄灭、施行气管切开术无法言语的情况下,常关心的的一个话题还是对人的尊重。他问病榻前的李阿姨:你……你辛苦……吗?孩子……们……对……对你尊重吗?听到满意的回答,他才安然睡去。
邻病房的一位老干部没有忘记,张乐平的病房最安静。每每探访的人来多了,老人又总是制止大声交谈——他心里始终想到周围的病人们。
在那段文化遭到唾弃的岁月里,漫画家本人被无耻的政治所漫画。
他像一个资本家一样胸前别着名牌,不同的是他的名字路人皆知,因此得每天清晨天不亮就悄然离家,赶到单位里去接受“改造”。繁重的体力劳动用来麻木艺术家的灵感,让三毛连同他的作者一起遭残。老人随时可以被呼唤批斗,悲苦的灵魂如同身上的痔疝一样火炙火燎。
有天,过了晚上12点钟,老人没能像往常一样踯躅进家门。儿子彷徨于父亲工作的报馆门口而不敢入内……最终才知道,父亲是在清除那积年笔战残留在墙壁上的标语痕迹,而认真地坚持到子夜。
一个冰天雪地的正午,电车因路滑而停驶,张乐平为了赶下午2点的班车去奉贤干校,提前午睡时间,把闹钟拨到12:15。儿子看到闹钟打闹时间提前了一刻钟,就按往常的习惯拨慢了一刻钟;另一个儿子看到父亲酣睡正浓,又把打闹指针拨到12:45。
这下误事了!张乐平蹒跚地赶到徐家汇,班车走了。据说,这辆车开往郊区途中翻掉了。老人并未庆幸自己逃脱厄运,心底常自埋怨这唯一一次迟到。
当大到南京路小到居室门框被刷上勒令“张乐平不许喝酒”的标语时,这位一贯循规蹈矩的好好人却用酒精燃点着生活的叛逆之火,如同无视当年反动派的恐吓之信。
他伏案写“检讨”,一边从小桌下掏出老酒瓶,咪上几口。
他还是需要酒。以致吸入性肺炎酿成大患后,受酒侵害的肝又大腹水。他的学生、《小兔菲菲》的作者杜建国在老师的遗容前特意放了一坛上好的黄酒,以祭先生在天之灵的嗜好。
漫画界老中青画家都推崇张乐平的人品画品,他艺术上权威地位的高坡,全是靠他自己用言行的高尚基石给予奠定。
大概是他自己遭受“运动”之厄尤甚,更其懂得用爱庇护别人。“文革”中到他那儿“外调”的人很多,他要么不说,要么就是说人好……粉碎四害之后,他将届古稀之年,主动提出要为党多多工作,甚至到友谊商店去售书。
1983年对他是个沉重的打击,艺术家的大腕由于帕金森氏症的影响而不能稳定地创作……每每作画,要费很打劲儿,用铅笔打样,然后改,然后定稿,一张漫画有时用一天也画不成。唏嘘再三,摇首叹息。
当新民大楼竣工时候,老人登楼远眺,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他是多么想回家画张画呀,遗憾的是最终为自己一生留下了最后一张照片!
那间画室由于连月的阴雨而显得晦暗。画桌上的一切依旧。床头上钉着的那幅少先队队旗如火一样鲜艳。那是1985年三毛诞生50周年时,少先队员们赠送给张乐平爷爷的礼物。队旗右上方画着三毛,四周写满了孩子们的签名,中间略大的一排字写着“三毛和我们在一起”。
躺在这张床上,老人每天和孩子们在一起。
夫人冯雏音告诉笔者,张乐平热爱儿童,他的作品反映最多的就是儿童题材。平时,他工作再忙,只要是孩子们的活动,他总尽量去参加,到少年宫辅导孩子画画、作报告。
27日那天,老人的故居来了许多人,那全是昔日邻居的孩子们。他们知道张伯伯过世的消息,前来痛悼老人,安慰亲属。许多与张乐平过去成为忘年交的近邻都能诉说这样一个往事:在阳光洒满的阳台上,张乐平画着画,然后问进来串门的孩子:这张画,你要不要?孩子高兴地收下了,有的甚至拿到过第二张、第三张——这些画陪同他们带着童年美好的记忆走向成年。张乐平的儿女们羡慕地对我说:连我们自己有的还拿不出爸爸过去的画呢!
他的画,大多送掉,留给自家的极少,凡有儿童索画,他是最乐于满足童心的这种奢望的。
世间唯名实不可期。散淡处世、一生清贫的老人每年都会受到世界各国名人录的通知书,他往往一看了之,几乎不回信。这并不会淹没这位大漫画家70年的辛勤耕耘。他的宣传画、年画、国画、水彩画屡屡获奖,他创作的三毛形象在中国已家喻户晓,蜚声海内外。
一个漫画家笔下的假想人物变成了生活中的真人,这是艺术的一种真正成功。
他的最宝贵的两部作品——
《三毛流浪记》,1983年捐赠给中国美术馆;
老人弥留之际念念不忘的《三毛从军记》捐赠仪式原定于1992年1月28日,因病情恶化而被推迟。向上海美术馆的这次捐赠仪式现已定于张乐平先生周年祭时隆重举行。
——摘自1992年10月9日《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