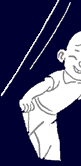
画图又识春风面
丰老久违了。一九七五年医院一面,竟成永诀,从此仙凡路隔,再也见不到我所仰慕的师长和朋友。近来看了丰子恺先生画展,看到那满堂的时代画卷,看到那透过纸面散发出来浓郁的生活气息,宛如又见到先生的音容笑貌。
早在二十年代,那时我在三马路望平街(即今汉口路山东路)转角的广告公司当学徒,偷闲常到四马路开明书店参观橱窗里的子恺先生的漫画。我被先生特独的中国风格的漫画吸引住了,以致流连忘返,真想能见一见我所敬佩的画家。
“一·二八”事变后,我开始画漫画,从此知道“漫画”二字就是子恺先生从日本翻译到中国的,更欲一识荆面,但总没有机会。一九三八年,当时我在武昌政治部第三厅所属的“抗战漫画宣传队”,经人介绍,有幸认识了子恺先生。那时他约四十开外,已养了长长的黑胡须,飘逸洒脱、和蔼可亲。后来我们又同到汉口上海书局对马路一家里弄的绍酒店一起饮酒。子恺先生为人风趣,谈笑风生,饮酒不多而笑声不歇。过些时候,只见他依桌垂头,鼻息浓浓,原来先生醉矣。这次画展上《客人持杯劝主人》、《我醉欲眠君且去》等画,不就是子恺先生生活的写照么?他的许多画,都是俯拾可得的平平常常的生活小景,但到了画家笔下,居然妙趣横生,耐人寻味。此后,我们又在小店相聚,饮酒谈天。先生学识渊博,使我得益非浅。他不仅是一位卓越的漫画家,而且是出色的音乐家、文学家、翻译家和诗人。我们在武汉相识不久,我就被派到安徽、江西一带从事抗战漫画宣传工作而分手了。直到解放后,才重新见面。有一次,得知先生患肺病在家,我前去探望,看到他正抱病学俄文,使我大为感动。此时先生年过半百,已经掌握了日、英、法、德四种外语,还要从头学习俄文,可知他的博大精深是来之不易的。
“文劫”时期,我们当然在劫难逃。因他是美协上海分会主席,沈柔坚和我是副主席,他挨斗,我俩总要轮流陪斗,坐“喷气式”,挂牌,一样待遇。有一次在闸北一个工厂被揪斗,我们一到,匆匆被挂上牌子,慌忙推出示众。一出场,使我好生奇怪:往常批斗,总是子恺先生主角,我当配角,而这一次,我竟成了千夫所指,身价倍增。低头一看,原来张冠李戴,把丰子恺的牌子挂到我的脖子上了。我向造反派头头指指胸前,全场哄笑,闹剧变成了喜剧。有时斗完之后,我们同坐一辆三轮车回家,彼此谈笑自如。有一次他问我怎样?我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我问他怎样?他笑着说“处之泰然。”后来有一次,我突然看到他那飘飘然的长白胡须被剪掉了。我很为他气愤,他却风趣地说:“文化大革命使我年轻了。”当然,这是酸苦的笑言。其实,他内伤很深。一九七五年九月,我到医院急诊,急诊处的同志悄悄地指指她后面空气混浊的观察室,告诉我丰子恺住在那里,我急忙过去,噙着眼泪拉着他那无力的手,不知所云,只是轻轻地拍拍他,表示慰问,要他保重……。谁知这是我和丰老的最后一面!
归功于丰老的家属和学生,冒着风险,千方百计保住了丰老部分遗作,使我们在劫后还能看到一代画师的遗墨。预展那天,我由儿子陪着,前去参观。当我拄杖站在丰老像前,睹物思人,不禁悲从中来,老泪盈眶。十年浩劫,摧残了多少艺术人才,洗劫了多少艺术佳品!在座谈会上,大家叹息、咒诅那阵狂风横扫了丰老的许多艺术珍品,但丰老的女儿却欣慰地说:“那时谁还想到有今天,想到我爸爸的画还能开展览会呢!”是的,“今天”来之不易,大家都要珍惜啊!
- -(摘自1981年5月20日 解放日报)